陈映真和肖斯塔科维奇

陈映真是台湾文坛少有的「知识型」和「信念型」的作家。他的知识领域不限于文学,更注重思想;他的基本信念也不限于政治,而更注重人道主义的人生意义。我和他相交多年,每次见面,都有类似的感受。
记得有一次,知名理论家詹明信(F. Jameson)受邀在台北的清华大学招待所演讲,我适在台北,遂前往聆听。

一进会场就见到陈映真,他态度严肃,像一个大学生,全神贯注地聆听这位马克思主义美学大师的论点,记得他事后又向我「请教」不少问题,我却答不出他想要求的答案。
陈映真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不断地在知识领域中求索,也不断地「确认」他的信念,我和他的友情,既亲切又「淡如水」,见面时他很少说应酬之类的话。
他的笑容是诚恳的,但说的仍然是严肃的话题:「最近美国的文学理论情况如何?」不只一次他这样问我,我也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心中甚感惭愧。有时默默无言之中,我更能感受到他那颗赤诚的心。
陈映真却从来没有问我关于他小说写作的事,反而是我屡屡劝他多写小说,时至今日我还是觉得他是台湾文学史上少数「大师级」的小说家。
他的作品早已成了经典,我在美任教时,讲到台湾文学必用他的短篇小说:〈将军族〉、〈我的弟弟康雄〉、〈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系列……这些作品都有英文译文,美国学生读来也受感染。
内中的那股情绪,更是陈映真所独有的,既崇高(甚至带有宗教性)又颓废(他用这种美学方式来批判台湾的「现代性」)。
但英文译文无法表现他那种特殊的文体;长长的句子,略带日文语法的结构,现西洋画的意象,哲学意味的内涵——这一切早已有行家指出,学界的评论文章无数,不必我再饶舌了。
但为了写这篇小文,我还是把他的两本小说集——《鈴璫花》和《忠孝公园》——拿来翻阅重读,不禁感慨系之。赫然发现,原来早在 20 年前他写〈赵南栋〉时,已经预知我们现今所处的资本主义的「人间」境地,以及它和革命理想之间的历史吊诡。

在小说中,赵南栋是终生信仰社会主义的革命烈士的遗腹子,长大后却成了一个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化身,他的生活愈放荡形骸、漫无目的,也愈反照出当年受苦受难的先一代人的高贵理想和节操。
妙的是陈映真在这篇小说中,用了一个音乐典故——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三交响乐,又名《五月一日》(劳动节)。在白色恐怖监狱中的烈士们就义之前,那位指挥家竟然用竹筷,指挥这首饱含普罗意识的交响曲。
乐曲开始了,「竖笛流水似的独奏,彷佛一片晨曦下的田园」,情绪转向激昂,「小号的朗敞刚毅的声音,像是在满天彤旌下,工人们欢畅地歌唱,列队行进。他感到了音乐这至为精微博大的艺术表现形式,是那样直接地探入人们心灵,而引起最深的战栗」。
这位指挥家张锡命专注、无我地挥划着指挥棒。「一场暴风,一场海啸;一场千仞高山的崩颓;一场万骑厮杀的沙场……在他时而若猛浪,时而若震怒的指挥中轰然而来,使整个押房都肃穆地沉浸在英雄的、澎湃的交响之中。」
我是一个乐迷,也是一个「肖迷」,近来每次聆听这首交响曲,就不觉想起陈映真小说中的字句,于是也学着张锡命用筷子指挥起来。
小说中的赵庆云落泪了,我也几乎落泪。这就是陈映真小说的魔力:他可以把这首肖氏作品中并不伟大的作品拉进小说世界中,而使得它听来崇高伟大。

我曾经问过他这是哪里来的灵感?他回答说是向音乐专家请教过的。
我觉得他的文学语言几乎超过原来音符的震撼,到了最后,「浑厚宽宏的合唱声,从地平线;从天际,带着大赞颂、大宣说、大希望,和大喜悦,从宇宙洪荒;从旷野和森林;从高山和平原;从黄金的收获;从遮天蔽日的旗帜,汹涌奔流,鹰飞虎跃而来。」

真不得了!这简直是史诗的笔法,但内中的意象却又像是音画对位的电影蒙太奇手法,我从中感受到鲁迅散文诗〈颓败线上的颤动〉的余韵。
多年没有见陈映真了,希望他现在的心情不像这首乐曲,那样沉重。也希望他早日康复,不久之可以共聚一堂,谈谈肖斯塔科维奇,或文学理论。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美在高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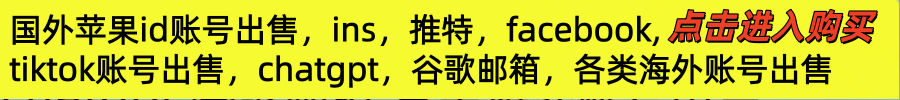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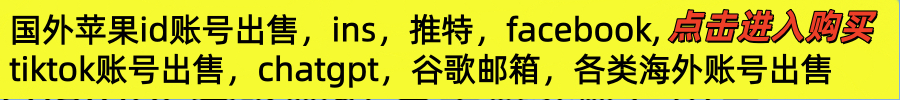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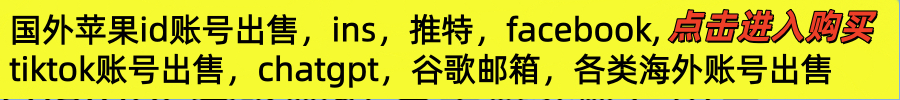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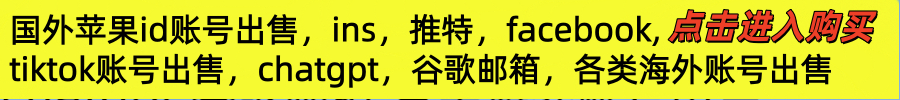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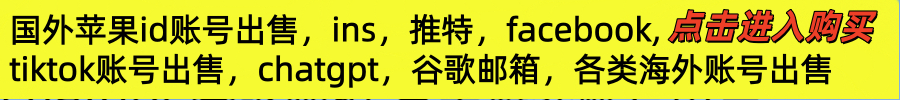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