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相过亲的三个男人,都死了
苏和是兰因镇整个九月里死的第三个男人。
算上九月初三死的张风,和九月十五死的王青善,都与李细禽相过亲。
因为这三人只是寻常百姓,案子自然由兰因县衙接手,李细禽则被当成是重要嫌疑人传唤过府。
作为七里堂有名的断案疯子,竟会因杀人案受到传唤,当事人李细禽自己都觉得,此生再遇不上比这更荒唐的事了。
惊堂木一响,本县新任县令苟精官腔立起:“堂下何人呐?”
李细禽倒是态度很好,一抱拳,朗声道:“在下兰因镇七里堂李细禽。”
“七里堂?可是那个专司江湖琐案的民间草莽。”
李细禽知道这县令是在拿腔拿调,故意小看七里堂,也不与他争口舌,只淡淡道:“若是大人非要如此说,那也不能算错。”
那苟精又一拍惊堂木,“本官问你,这三名死者与你是何关系啊?”
“回大人,在下曾于九月初三、九月十五,还有九月二十七,与这三人在琵琶街口的晴月楼吃过饭。”
“本官再问你,因何缘由啊?”
“在下奉七里堂堂主李松之命,与他们在晴月楼相看。若是各自有意,还家之后,便可商量交换三书,开始准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迎娶之事了。”
这苟精月前才新到兰因镇任职,七里堂李姓母女的事迹他只粗略听说过,本想着拿捏些强调给这李细禽点颜色,却不想得了这样一番回答,不觉有些乱了阵脚,再一拍惊堂木,不耐道:“本官哪里是问你这个了?”
李细禽面露天真:“那大人问什么,难不成是想问这三人可是被我所杀?”
苟县令自然知道李细禽是凶手的可能性并不大,只是奈何眼下并没有其它证据,只好胡乱抓个线索胡乱审理,也算证明自己在努力办公。
“你最好将自己何时何地与这三人见面,见面之后又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老老实实交代清楚,否则……”
李细禽看穿了这苟县令的心思,懒得再装,冷笑道:“否则什么?”
苟县令看出堂下那女子细目中明晃晃的嘲讽,登时大怒,站在他身旁的县尉李立急忙凑上来在耳边说了几句。
这李立是本县的老人,颇为油滑,苟县令听了他几句,立刻对着李细禽道:“否则本官就判你因与这些青年男子相看不成,老而难嫁,心怀怨恨,对他们痛下杀手!”
“铛”,一道寒光闪过,苟县令猛地一震,就见一枚匕首正贴着自己的面孔飞过,钉在了后壁墙板之上。
“抱歉,手滑了。”李细禽收了手,“苟县令若是没有旁的事,在下就先走了!”
“大,大,大胆!来来人呐,给我把这个悍妇拿下!”
堂上众多差役当即要动手,李细禽微向后一退,攥了拳。
她上堂之前解了兵器,唯一藏在靴筒里的匕首还被她钉了出去,眼下倒多少有些苦恼,她的拳法凌厉,不好乱用,想起出门前娘亲还特意叮嘱她不要与县衙起冲突,可谁也想不到这县令忒气人。
正在这时,却听堂外传来一声清丽女音:“住手。”
李细禽转头,只见一个身穿灰麻细裙的女子站在堂下。
女子肤若白瓷,眉目静秀,眼角悬着一滴朱砂泪痣,乌发结成粗辫,被一根红绳系住,停在胸前。
却是李细禽前些日子才认识的林宿。
这林宿本是个药娘,新来镇上不久,开了一家果子铺,卖些药膳果子,生意不温不火,日子倒安宁恬淡。
苟精小眼一眯,“你是谁?”
林宿见礼,“小女子林宿,是张仵作令小女子来与大人呈报验尸录的。”
“验尸录?本府怎么不知本衙的仵作是个女子?”
“小女只是与张仵作在学艺,并不是堪录入籍的仵作。”
苟县令瞥了一眼站在他身侧的县尉,李立弓腰驼背地急忙凑上去又嘀咕了几句,苟县令复又看向堂下一黑一灰两名女子,稳了稳心神,故意拉长音调道:“那就把验尸录拿给本官看看吧。”
林宿微微颔首,将手上一本蓝皮簿交与县尉,然后继续道:“李风,死于九月初三酉时到戌时之间,尸体口眼张开,面部呈紫黯之色,眼角有血线,唇色紫黑,舌头僵硬,手足指甲青黯。
“鉴于身上并无其它伤痕,应该是中毒而亡,我们查看了他当日的饮食,发现了河豚,但不排除还有其它毒物。”
苟县令翻着手中的验尸录,略微抬眼,就听林宿接着又道,“据晴月楼老板和店中茶博士所说,李细禽是大约午时和张风在店中用餐,但一刻之后就得知江洋大盗紫衣儿出现在了距离兰因镇十里外的绿柳山庄,她便速往绿柳山庄去了。紫衣儿现就在县衙大牢,大人可去讯问。”
苟县令一把拍上了验尸录,怒道:“你什么意思?”
林宿不慌不忙,接着道:“王青善,死于三月十五日戌时,被人用利器从前洞穿胸肺致死。
“他死时,李细禽正跟随七里堂堂主李松要如何诱捕紫衣儿一事,来县衙拜访大人,不过大人并不把那江洋大盗当作什么,对于七里堂也不甚了解,将二人晾在县衙外堂,直到亥时末。
“李细禽在次日午后,自行捕获了紫衣儿,再度来县衙,与县令商讨如何羁押等事宜。”
李细禽看着林宿不紧不慢,心中笑得直打跌,面上还算镇定,一本正经地对林宿道:“这些东西验尸录上不是都有,你这背一遍是什么道理?”
林宿更是严肃,对李细禽道:“我担心苟县令不识字。”
苟县令当即将验尸录一把摔在了桌上,大怒:“给我将这两个悍妇都抓起来!”
却见林宿再度转身,对着苟精道:“当然了,小女更怕苟县令到期破不了案,等自京城而来的赵知正赵巡按到了兰因镇,苟县令就得解释自己花了多少钱才捐到了自己这顶乌纱。
“听说那赵巡按乃是永和二年的榜眼,初仕就在御史台,后又有监察百官之则,为人极为刚正不阿。”
话说得慢,动作也很慢,林宿从腰间解下荷包,从里面翻出一枚白玉小印,放在了苟县令的面前。
李细禽知道林宿父亲官至宰辅,她虽早与家里断了联系,但想来幼年时多少也受了些熏陶,对这些事总比自己一个江湖草莽要熟练。
李立急忙上前查看,却见小印上刻着“我本山人”四个小字,压低声音对那苟县令道:“听说赵巡按的私印正是这四个字。”
苟县令眼珠兜了一圈,正要开口,却看堂下急匆匆跑上来一名皂班小吏。
这小吏到了堂上,倒是先定了神,环视四周一圈,才对着苟县令道:“启禀大人,又出命案了,有仆人发现城南柳家公子,死于花园之中。”
“柳家?可是那个绿柳山庄的柳家?”
小吏点了点头,“正是绿柳山庄的柳氏七子,柳庄。”
“柳庄?”苟县令立刻看向李细禽,“你不要说此人与你没有干系?整个兰因镇都知道你们的关系!”
李细禽一时也僵了脸,因这个柳庄曾在十日前,站在七里堂大门外立下宏愿,此生非她不娶。
虽然有许多不在场证据,但李细禽也知道,自己与这几起案子脱不了干系。
好在苟精受了林宿一圈官场人情的恐吓,眼下也只能令李细禽不得随意离开兰因镇,以待官府随时传唤。
眼看着县衙中人匆匆去了绿柳山庄,李细禽捉了林宿,问道:“你怎么会在这儿?”
“堂主说张仵作的验尸本领极高,我便来学了。”
“你不好好开你的果子铺,学什么验尸?”
“技多不压身。”
李细禽知道林宿此人从来主意端正,凡是她想做的事,莫说天王老子,就是娘亲李松也是没有一点办法的。
林宿倒是略有些诧异地看向李细禽,“死的这几个人都与你相看过,你难道不想知道凶手到底是谁?”
李细禽道:“想找凶手还不简单,我在想如何能一箭双雕。”
双雕?
林宿知道李细禽不仅有断案之能,惹祸裹乱也不在话下,不免对那只尚不知名姓的“雕”儿生了几分杞人忧天之心。
话虽如此说,李细禽到底还是运上轻功,赶在县衙诸人前面到了绿柳山庄。
她并未自行询问,反是隐身在山庄层层叠叠的绿柳之中,端看那苟大人如何问话。
柳庄的尸体是清晨时,被洒扫庭院的小仆,发现浮在后院水池中。
说是前一夜柳庄从外面喝醉了回家,到了家中仍旧酒兴不减,令手下小厮又拿了几坛酒要在屋里饮。
不过待小厮拿了酒到了房里,发现少爷已经鼾声四起,遂几个人将少爷搬上卧榻,盖了被子,便出去了。
没人看到他是何时出的卧房门,亦没人看到他是如何走到水池边,直到早上发现了尸体。
苟大人遂问那小厮:“你半夜就不曾听到一点动静?”
小厮低着头:“我……我见少爷睡得沉,我也就去睡了,昨夜雾很大,我感觉自己也昏昏的,睡得很沉。”
苟大人问:“那你可知你家少爷是同谁喝酒去了?”
小厮道:“就几个昔日同窗,先前都在玉门书院读书的。”
苟大人想了想,又问:“你家少爷是何时出去喝的酒?”
小厮答:“午后便出去了。”
“那何时回来的?”
“戌时末,将近亥初了。”
苟精点了点头,那柳庄的父亲柳公便迎了上来,许是儿子陡然罹难,整个人也变得枯朽许多,只弓着腰探问案情。
可这苟大人也实在说不出什么,只道:“还请节哀吧,这令郎到底是醉酒后失足落水,还是被人谋杀,还得等仵作验过尸才能判定。”
那柳公面若风干的酸枣,又怒又哀,哑声道:“苟大人,我已听说镇上接连死了几个青年男子,都曾与那七里堂的悍妇李细禽相看过。那李氏女武艺高强,定是她趁夜潜入我柳府,将我儿推到水中。还请苟大人替我儿做主啊!”
苟精听到此话,只觉这推论也甚是合意,立刻情真意切地拍了拍柳公双手,道:“柳公放心,不过一介江湖草莽,我定拿下!”
隐在高处的李细禽不觉眯起了眼。
她的心眼不算大,眼看着这些家伙不遗余力地想往自己身上泼污水,只道若是想破这案,一箭双雕怕是不够,至少得一箭三雕。
在林宿跟着县衙张仵作给柳庄验尸之时,李细禽在街口的茶苑里寻到了正在听热闹的巫小鸾。
这巫小鸾乃是本镇有名的神婆,凡镇上人家里有红百事,她便去给人家跳大神,加之她又天生好打听,遂这镇上凡大事小情,都没有能逃出她耳朵的。
茶苑里的热闹自也与新死了的几个青年公子有关,许是李细禽杀人这个段子缺点艳色,众人已经将杀人的真凶锁定在了凰儿山里狐狸精、蜘蛛精、蛇精,以及兰因镇红衣女鬼的身上了。
巫小鸾听到兴奋处,忍不住就自己撸袖子上场了,道:“我告诉你们啊,这兰因镇的女鬼啊,共有八十七个,麻衣鬼,青衣鬼,白发老妇鬼,说了你们也不知道。
“单说喜穿红衣的这个,那是西河街头韩家二女,她前些年被家中后母嫁给了卢老头做妾,出嫁当日想不开,吞金了。
“她后母现在每日惶惶,总说身后发凉眼前发红,就是这韩二姑娘化成厉鬼,总跟着她。”
当即有好事者问:“那韩二姑娘,为何要杀这几个男子呢?”
巫小鸾道:“这事啊,还真就我知道。想当初我本是要替韩二姑娘做媒的,这几个男子啊,说来啊,都是本镇上有名的好郎君,要不然那七里堂的李……”
“咳。”
一声轻咳,巫小鸾转身,听见嗽声,就见黑发黑目一身黑衣的李细禽正笑着看她。
茶苑众人见李细禽到,一时也都没了声音。
巫小鸾眼珠一转,转头扬声道:“我们七里堂李大姑娘,那可是智勇双全,武艺高强,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李细禽代母探案,这叫什么,这叫雌兔本英姿,雄兔靠边站!”
李细禽只怕她再说出什么怪话,急忙道:“行了,行了,快下来吧。”
巫小鸾见她不恼,立刻凑过来,“怎么着,想去从新县令手里抢案子?”
李细禽瞥了她一眼,“你怎么知道?”
巫小鸾道:“废话,别说是你,我都想去查查,到底是谁敢往咱们李大神探身上泼脏水!”
李细禽不想听她叽里咕噜再说怪话,只道:“林宿正在替柳庄验尸,我们去她的果子铺里等她。”
巫小鸾一惊,“林宿?她怎么去验尸了?”
“她的心思,天知地知,你不知,我怎知?走了!”
一路行至运河边,林宿的果子铺仍旧关着门,二人只好先在河边一小亭中坐下等候。
恰见一个女子拉着一辆水车要过桥,那女子身量娇小,拖拽水车时挣红了脸,李细禽远远瞧见,几个跃身,落在那水车后面,双手往前推了一把,水车总算过了桥。
女子转身看向李细禽,比划了几个手势,李细禽摇了摇头。
那女子又冲她鞠躬,然后才拖着水车缓缓去了。
巫小鸾道:“这不是哑铃吗?她怎么又开始卖水了?”
“哑铃?”李细禽看她,“你认识?”
巫小鸾点头:“她刚来镇上就是我帮她找的工,前几日见她,还在丽景楼替姑娘们洗衣裳呢。她说不出话,我也是大概知道她应该是逃难来的兰因镇。”
“逃难?”李细禽诧异,“这附近何处遭了灾?”
巫小鸾摇头,“她是个哑巴,说不清楚,但人真的是能干,后厨里能帮工,穷汉街上能缝补。别看身量不大,她还能踩高跷,耍把戏,玩杂技。
“我最早推荐她去浅枫染坊里替人染布,一个人能顶三个人的工。不过因为她是女子,又是个哑巴,好些人说她不吉利,总是干不长久。”
李细禽身为女子,在七里堂断案这么多年,自然知道一个女子想要独自讨生活的不易,只道:“倒真是艰难。”
巫小鸾哂笑:“人在这世上活,本就不是易事,落到女子身上,更是难上加难。可无论怎样,既然已经活着,就只能继续不容易地活下去。难不成,还有得选?”
李细禽倒是少见巫小鸾这般神情,她知道这巫小鸾本是个孤儿,不知为何被父母遗弃,被庵里几个尼姑养大,后来混迹街头,自己给自己讨生活,想来也惯看这样的人事。
她遂也不再追问,只道:“苏和,张风、王青善、柳庄,这四人到底什么关系?”
巫小鸾立刻从怀里摸出一本簿子,鬼眉鬼眼地笑道:“嘿嘿,就知道你要问,早给你准备好了!”
李细禽狐疑地接过那簿子,却见靛蓝封皮上写着“兰因俊男名录”。
“这什么东西?”
“这可是我花了五百个铜钱从孙媒婆那里买的,媒婆秘籍,冰人宝典。其实还有本兰因秀女名录,不过感觉没什么用,我也没钱了,就没买。
“不过咱们这镇上原本就是适婚的男子多,待嫁的女子少,咱镇上的媒婆都有些走南闯北的本事,能将外乡女子说到咱镇上来,周边许多地方的媒婆都将咱兰因唤做郎君乡呢。”
李细禽随意听着巫小鸾说些有的没的,一边翻看将那名录,却见里面果真都是些本镇适龄婚嫁的男子,一页绘有绣像,另一页则标注了姓名、生辰、籍贯,家中房产、学问深浅,以及个性趣味等等,果真是个媒婆宝典。
巫小鸾将那簿子拿回来,翻到中间一页,指着“兰因十二郎君”一行道,“这几个人,都在这个兰因十二郎君的名录下,乃是这名录中最为优质的十二名男子。所以要我说,这个孙媒婆还真是对你上心,一出手,就是四位公子啊,可惜了……”
“这十二郎君,是媒婆们评的?”
“那倒不完全是,因着那一年咱们兰因镇乡试,恰好是这十二个人都入了围,加上他们都前后脚地在玉门书院读书。
“其实这些人彼此间交集算不上深,只是媒婆们好编纂名目,就将这十二个放在了一处,若谁能替十二郎君公子都说上一段好姻缘,那说出去,谁还不巴巴请她做媒?”
李细禽这才恍然,只是一时也想不明白凶手为何会按着媒婆宝典杀人,亦或是这几人还有旁的关系也未可知。
她又仔细翻了翻那俊男名录,将那十二郎君的来历背景一一记下。
林宿直到掌灯时分才回来,见二人等在门外,知道她们的来意,也不多话,先开了门,容她们进屋,又去将自己清理一番,才回到前厅。
厅中弥漫开一股淡淡的青松水汽,似是她新熏了香。
李细禽知她素来寡言,也不多说,方才等待的这阵功夫,已从她惯吃的面店里打包了三份阳春面,又要了几个小菜,并两坛木兰春,且等着她落座。
巫小鸾早已经饿了,不想她刚端起碗,就听林宿道:“柳庄口鼻内有水沫,还有一些小而淡的血污,脸侧有磕擦,腹内急胀,可以确定的是生前溺水而亡。只是他手握而眼合,似是自己投水。死亡时间该是昨夜子时,尸体泡了整夜。”
“自己投水?”李细禽困惑,“十日前他还想娶我,十日后便想不开要自己投水了?”
巫小鸾看着眼前的面汤,只觉那面汤变成了泡尸体的池水,一时间没了胃口,悻悻道:“那如此看,这柳公子对细禽姐还真是用情至深啊。”
李细禽看她,“你也算是惯看男女婚丧,你自己相信吗?”
巫小鸾看她表情肃然,讪讪道:“那一时冲昏了头脑也是有的,只是他可能没撑到幡然悔悟罢了。”
林宿没有理会她们胡言乱语,又道:“柳庄昨夜身死之时,是雾天,但因为他的尸体从水里发现,所以这个线索看起来没用。但我发现王青善的衣服上也有潮气,便去问了更夫,据他说,这几个死者死时,竟都是夜雾天。”
“雾天?”李细禽略一迟疑,“你的意思是,凶手故意选在雾天杀人?是因为雾天容易隐藏踪迹?”
“这只是尸体上的线索,具体为什么,我说不好。”林宿继续道,“还有,我自柳庄鼻息间有一些细白丝絮,暂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这东西在之前二人尸体上,可有发现?”
林宿道:“我在验过柳庄之后又回头去验了那三具尸体,苏和与王青善的身上都没有发现,只有李风的喉管处有两缕白丝,说像又不完全像,毕竟类似的东西很多,譬如动物的毛发,植物的细丝,都有可能。
“若非要抓住这个线索,那就得将四人的尸身剖开,打开胃袋,观其肺,查其脾,只是张仵作并不愿开尸,我不是仵作,做不得主。”
“剖尸确实是大事,若非到不得不剖之时,我倒可以去和张仵作周旋。”李细禽继而又问,“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怪处?”
“王青善尸体上只有一处贯穿的致命伤,只是那个伤口不知道为什么,似乎过于平整了。”
林宿在胸口比划了一下位置,“假设对方是一个武功极高之人,忽然出现,王青善来不及躲闪,凶器即可贯穿,似乎也说得通,只是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的武功。”
李细禽在自己所知的武功路数中盘了一圈,摇了摇头。
林宿接着又道:“如果对方就只是一个寻常人,王青善至少在凶器刺入身体时会痛到挣扎,伤口周边也会有些一些印记,或者人在情急之下用手去拦挡,也会留下伤口或者印记,但王青善的那个伤口……太平静了。”
“平静?”李细禽咂摸着林宿的用词,“除了武功极高瞬间贯穿之外,若对方是他认识的人,他没想到对方会杀他……或者……”
因为线索不够,李细禽一时也不敢妄加推理,只担心一不小心就落入某些自以为是的执念,遂又问:“那苏和据说是夜中坠楼而亡,你可在尸体上发现什么了?”
林宿想了想,“因为正面有许多擦伤,只能判定他是正面摔到楼下的,所以若不是他自己坠楼,便是被人推下去的。”
“他坠楼的现场我已经去过了,他坠楼之后家中人恐惧,做了一场法事,现场已经没有痕迹了。”李细禽想了想,“眼下唯有绿柳山庄,许还有些线索。”
林宿点头,拿起筷子,“吃罢了,我与你同去。”
巫小鸾也急忙道:“我也去,我也去!这种事你们不能抛下我!”
李细禽道:“带上你当然可以,不过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做。”
巫小鸾急匆匆将面条卷进肚子,推了碗,道:“知道,兰因十二郎君,谁和谁有仇,谁和谁有怨,手拿把掐,手到擒来,交给我,保管给你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入夜,绿柳山庄挂着白幡与祭灯,时有风声将哭声送出。
李细禽白日里听到那柳公与苟县令的对话,知道自己早已被他们视为凶手,想要堂而皇之进去查案自是不大容易,可又担心若是不能趁早,那现场被人走来走去破坏了,定会失了线索。
巫小鸾眼珠一转,“这个容易,我来引他们注意,你二人只管去后院探查。”
李细禽皱眉,“你能有什么办法?”
林宿道:“她是神婆,神鬼之事,自能引人。”
李细禽想起白日里巫小鸾在茶苑里起的那一场热闹,不觉莞尔。
巫小鸾得了二人的首肯,兴冲冲跑回了家,脸上扣着一张靛蓝招魂傩面,披挂上五色彩条大袍,腰间拖挂了八卦盘、铜镜、铃铛,手中持了一根大漆百铃杖,叮铃咣啷,竟是比她本人还要聒噪些。
此时已是亥会时分,所谓人物俱无的混沌时刻,九月的天气,又起了大雾。
守灵人一时都有些昏昏,风摇着冥灯,忽而间就传来一阵渺铃声。
为柳庄守灵的两个族中兄弟猛地一惊,接着就听一个沙哑低沉的声音自府外传来:“柳庄,柳庄,你为何不速速去地府报道?”
跟着这两个兄弟就又听见一个声音,这声音却极为熟悉,正是他们堂兄柳庄的声音:“本山府君大人容禀,地府说柳庄身负血债,还牵累旁人受冤,不许柳庄过桥啊!”
这二人闻声一惊,急忙冲出去,就见黑夜之中,乱铃声响,庄外有一神婆,一时立,一时跪,一时问,一时答,身体里仿佛装了两个灵魂般。
一个胆大些的呵斥道:“兀那神婆,做什么怪事?”
巫小鸾浑然不觉,忽而跪倒在地,哭道:“那水实在太冷啦,顺着我的口鼻,我喘不过气啊,可那害我之人,我还未看清他的样子,我冤啊,冤啊!求求上差,至少让我知道是何人杀我!”
另一个胆小些的则哆哆嗦嗦道:“这……这这……这确实堂兄啊……”
这动静不小,一时间柳庄中人都知道柳庄附身了一个神婆回家来了,登时倾巢,皆都出门来看。
李细禽一边同林宿摸黑往后院走,一边小声道:“想不到小鸾还有这等口技。”
林宿道:“她替人家跳大神,若是不能模仿死者声音,对方如何相信是魂灵附身。”
李细禽又道:“若不是要去查案,我倒还真想看看这家伙能要如何演。”
林宿催促:“行了,快走吧。”
虽然这柳庄也算是曾拜倒在李细禽玄墨劲装下,李细禽对他却实在知之不多。
只是记得与他相看吃饭时,他是如何手舞足蹈地讲着“十步杀一人”的李白、白虹贯日的荆轲与聂政,鱼腹藏剑的专诸,还有盗盒的红线、剑术极高的聂隐娘,总之就是对江湖的痴迷已达疯癫之态。
待进了他的卧房,这种感觉更是扑面而来,墙面上挂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书架里头一本就是刺客列传。
李细禽在翻检床铺时,竟还在他的枕头下翻出一本未写完的残卷,名曰“兰因英雄儿女传”,头一人写的就是兰因女侠探李细禽。
李细禽略读了几句,满目皆是溢美之词,着实有些尴尬。
她将那残卷放回,转身就见林宿正在香炉边细嗅,遂问:“你发现什么了?”
林宿直起身,跟着却忽然一晃,竟险些要跌倒一般,李细禽急忙上前将她扶住,问:“怎么了?”
林宿摇了摇头,没应声。
李细禽道:“是不是累了?也怨我,这么着急将你抓来陪我查看现场。”
林宿仍旧不语,只看着那香炉,过了些许时间,才道:“你将这香灰装一些带回去。”
“香灰?”
李细禽忍不住也凑到香炉边闻了闻,却并未闻到什么,只按林宿吩咐,装了些香灰揣在怀里。
二人跟着又在屋里细查了一圈,没有发现更多线索,便出门顺着柳庄当夜行进的道路,往溺死他的水池边走去。
因着白日来了许多人,脚印已然纷乱不堪。
林宿蹲在柳庄跌入水池的地方查验,只发现了一些散碎的石块,倒是与验尸的结果相似,那柳庄似乎正是自己投入池中的。
林宿不觉又想起其它几具尸体,一种奇怪又无法描述的感觉从心头浮现。
李细禽则绕着水池细查,一圈之后,只在水池的另一边,发现了两个圆形印记同一支黑色的羽毛。
李细禽捻起那根羽毛端详,似是一根鸦羽。
二人比对了线索,只道这柳庄虽看似是自己投水而亡,可说来他并没有什么轻生的动机,只说他因醉酒失足,倒也说得通。
奈何他连同前面那三人偏偏都和李细禽有关系,而且又都在“兰因十二郎君”的名单里。
山庄前院传来一阵骚动,李细禽对林宿道:“小鸾演不了多久了,我们先离开,再做打算。”
林宿点头,李细禽环住她的腰身,纵身一跃,便出了山庄。
山庄门口,巫小鸾横躺在地,无论周围人如何喊叫,都不发一言。
终于,庄子里有个老妇端着一盆红汪汪的不知是什么的冲了出来,泼在了巫小鸾身上。
巫小鸾当即坐起,先是环顾四周,跟着用了她原本的声音:“咦,我怎么在这儿?”
诸人皆不语,只看着她四下探看一番,自言自语一般,“绿柳山庄?哦……原来是柳郎君附了身啊。”
说罢,她又站了起来,因着身上还滴着红,围观诸人急忙向后退散,她倒是不以为意,只问:“可见到你们家的亡人了?”
先前那个胆子略大的守灵族亲说:“你说的亡……亡人,可是我堂兄,柳庄。”
巫小鸾随意道:“应该是吧,我不知道,这亡人借身,我通常都是没有知觉的。他可与你们说了什么?”
“他……他只说,只说自己是冤死的,但说他没看清杀他之人的脸,让我们一定为他查明真相。”
“哦,这样啊。”巫小鸾一本正经地想了想,“此事是他阳间的债,若是不能还完,恐怕地府是不会收他的。”
这么一会儿时间,柳府中已经有人认出了巫小鸾的身份,知她是有名的神婆,最擅请鬼上身,柳公遂道:“敢问巫家,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呢?”
“替你儿查明真凶,将原委写在黄纸上,烧与他知。”
“那杀人的,正是七里堂的那个悍妇,李细禽啊!”
巫小鸾却道:“柳庄自己可说是她了?”
守灵的一个族兄说:“方才我听堂弟说,说没看清凶手的脸,还说牵累旁人受冤,所以地府才不许他过桥的,这是什么桥啊?”
“自然是奈何桥啊。”
众人一听,当即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唉……”巫小鸾又深深叹了一口气,“你们这样都没听明白吗?你们所认定的凶手压根就不是真凶,咱这兰因镇上能破奇案的还非得她莫属,你们若得罪了她,这柳庄就只能当孤魂野鬼了。还是劝你们,好自为之吧。”
巫小鸾说罢,一甩大袖,叮铃当啷地转身就走,只留下柳府上下一干人等,面面相觑。
等李细禽和林宿终于在拐角暗处等到了款款而来的巫小鸾,二人不觉都掩上了鼻子,李细禽问:“那老妇到底往你身上泼了什么?”
巫小鸾道:“公鸡血啊。”
林宿面色发白,李细禽便挡在她与巫小鸾之间,她知道林宿虽能耐着性子验尸,可一出了仵作间,对血腥味却是半点也闻不得。
也不知是因为苟县令忙前忙后几日也得不出什么结论,还是因为巫小鸾那夜的出色演出,四日后,绿柳山庄竟往七里堂送了满满一封银铤,希望七里堂能出手缉凶。
堂主李松命人将银锭送回,只道七里堂所辖只是江湖悬案,这类案子只能经由县衙督办。
孰料柳公竟又修书相求,只道他儿柳庄,素来钦羡江湖侠士,奈何因幼年体弱不得习武,遂抱憾半生,可他的心是属于江湖的,遂也当被视作江湖中人。
巫小鸾略一打听,便知道了柳公与儿子的心结。
说这柳庄本于读书一途极有天赋,就连玉门书院的周夫子都夸他定能金榜题名,奈何他的心思都在那些侠客身上。
柳公恨铁不成钢,苦口婆心地劝了,暴跳如雷地打了,总之什么法子都用尽了,不想这柳庄不仅不悔改,还扬言要娶李细禽。
柳公又气又怨,这才在柳庄死后,将怨气尽数倒在李细禽身上。
听了这么一段,李细禽忍不住又想起那间摆满了兵刃的房间,以及那本未写完的侠客传,心中倒生出几分恻隐,便去与李松道:“此事虽不是江湖悬案,但既与我有如此深的牵连,我不能不管。”
李松道:“自古江湖不可涉庙堂,你管倒是能管,只是京都不知多少人盯着七里堂,若苟县令若以此上报,待朝廷以枉涉司法的名义废了七里总堂。
“你娘亲我倒是没什么,也就是带着你另寻个去处,另谋个营生罢了。倒是你,比较麻烦。”
“我?”
“你这样爱断案子,可又因是女子做不得县衙的捕手,难不成你想女扮男装去考进士?可是你又不爱读书。”
“娘!”
李细禽从来都知道自己说不过娘亲,可这样听来还是多少有些气人。
李松倒是仍旧面色寻常,只道:“你有这功夫,倒是不妨去县衙审一审那个江洋大盗,他是江湖中人,你管一管也不妨事。他老在夜里偷东西,最近颇多雾天,这厮身手稀松,眼神倒是不错。”
“雾天?”
李细禽忽然想起那日偷偷在柳府听到苟精的问话,仆人说柳庄醉酒回家,夜里正起了大雾。
先前林宿说起其余三人死亡之时,竟无一例外,夜中都起了水雾。
想到这一节,李细禽立刻就要往县衙去,不想又被李松唤住,随手抛给她一个卷轴。
李细禽诧异地接过卷轴,就见封处写着“失宝名录”。
她略略一想,就明白了李松的意思,这名录中涉及数位江湖名宿遗失的宝物,既然有了紫衣儿这大盗,少不得得去审问一番。
李细禽忍不住对娘亲深深一礼,“我李细禽真是三生有幸,得了您这样一位好娘亲啊!”
那李松亦不抬眼,只慢悠悠道:“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苟精坐在后衙大堂,上火牙疼几乎要了他半条性命。
说来他也是花费了大半身家才捐了这样一个小小县令,还没等想好怎么把钱给捞回来,就遇上这么四桩命案,且还都是本地名门望族的青年才俊。
不仅如此,他亦从州府得了消息,那小小药娘所说的李巡案确实不日就要到他的治下,若被他知道了自己完全没办法破案,那丢官事小,脑袋能不能保住都两说呢。
李细禽要审紫衣儿的事正就是这时被报了上来。
苟精当即挥手:“不许不许,什么七里堂,那紫衣儿既然已经收押在县衙,就是公家案,与她们何干?”
随行在侧的县尉李立却眼珠一转,凑到苟精身侧,低声耳语了几句。
那苟精听罢,眼皮一翻:“若是她能令那紫衣儿认下此案,但之后又死了人,该如何?”
李立道:“到时我们就可说是她办错了案,将七里堂赶出兰因镇,然后我们再向上奏报,说杀人的就是她李细禽,反正有她与那几人的关系在手,是或不是,等将水搅浑了,上面人再想查,怕是也难得很。此案本就令人费解,做成悬案,轻而易举。”
苟精头回当官,不比李立老练,一听之后,正要点头,忽又一顿,坐直了身子,道:“此事我还须再想想,就先让她去审吧。”
李细禽自然不知道两人算着什么,只是见娘亲为她的“深远计”没派上用场,竟还有一些失望。
紫衣儿毕竟也是个江洋大盗,苟精不敢松懈,将他关在大牢深处,又以精铁链将他的脖颈与四肢尽数扣死在墙上。
他吃喝拉撒尽数被困,着实是苦不堪言,远远看见来人,急忙喊道:“快点吧!你紫爷爷快要渴死了!”
李细禽一听,顺道拿了壶水,令狱卒打开牢门,一曲腿坐在桌上,笑盈盈地看着紫衣儿。
紫衣儿一见来人是李细禽,立刻合眼闭嘴,不再叫渴。
李细禽笑:“不是渴了吗?我这不是给你送水来了。”
紫衣儿仍旧闭着眼:“我就是渴死,也不喝你这小妇人的水!”
李细禽点了点头,提起水壶,将满满一壶水倒在了地上。
那紫衣儿听见水声,立刻睁眼骂道:“你个贼妇人!竟然这般心狠手辣!”
李细禽笑:“要说贼,那小女可不敢在前辈面前称贼。”
紫衣儿冷哼一声,并不搭话。
李细禽又道:“小女此来,是有事相问。”
紫衣儿道:“没什么可说的,我那日是状态不好,跑肚拉稀,才被你给捉了。要不然我能被你个区区小妇拿下。既然被捉,我也自认倒霉,但你若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李细禽想了想,笑道:“方才紫老前辈说,是因状态不好才被小女捉了?”
“哼,不错!”
“那若是前辈状态很好,却仍旧被小女捉了,那待如何?”
“你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小老儿定然竹筒豆子给你倒个干干净净!”
“一言为定!”
“什么意思?”紫衣儿一惊,“你是说你要再和我……比一比?”
“没错,就是前辈所想。”李细禽拍了拍手,从桌子上一跃而下,“来呀,给前辈整治酒菜,吃饱喝足,我与老前辈再行比过!”
狱卒们面面相觑,腿快的已经去报了苟精。
就在苟精想要骂人之时,得了李立的耳语:“这不正好顺水推舟?”
苟精一想,正是如此,遂正色腆肚,扬扬手道:“这些江湖匪人,行事从来都出人意表。罢了,就按她说的办吧。”
紫衣儿万没想到还会有这么个机会,所谓绝处逢生,自然喜不自胜。
李细禽交给他一个兜子,里面装满了石灰粉。
“还请前辈背着这个石灰粉包。我们以福缘寺山门为终点,谁先将石灰粉抹上寺门外的大狮子,谁就算赢。”
那紫衣儿想了想,将石灰粉包背上了身,道:“你这小女子惯会使花招,若我所料不错,你这玩意儿定要防着我老头半路偷跑,怎么防我不知道,但肯定就是这样的!
“你既然以小女子之心度我大盗贼之腹,老头我还非得说话算话,若是我半途逃匿,你大可去江湖上宣扬,我一世贼名,甩在脚下,任凭你踩!”
李细禽见紫衣儿洋洋洒洒这么一堆,总结起来不过就是拉不下面子好个声名,遂一抱拳,“前辈一诺千金,小女记下了!”
问讯来看热闹的巫小鸾和林宿悄悄打赌:“阿宿姐姐,我打赌,那贼老头肯定半路会跑!一百文,赌不赌?”
林宿道:“一千文,不仅紫衣儿不会跑,还会有案子线索送上门。”
巫小鸾占了半张脸的眼睛瞬间变大,速速摸出钱袋:“赌了赌了,小亏大赚,阿宿姐你可真是我亲姐!”
二人刚定了罢了赌约,另一边,一黑一紫两道风影,转瞬便跃上了兰因县狱前的两排商铺的鱼鳞屋顶,各自一窜既有数尺之远,不多时就消失在了房檐尽头。
紫衣儿既是扬名的大盗,轻功自然不俗,他曾于一处绝世之所寻得“八步赶蝉”的秘籍,从此之后便做了大盗,借此扬名江湖。
只是他却没想到,无论他速度如何快,那小女子竟始终坠在他半步之后,步法虽一时看不出什么玄妙,可足下劲力却长,再看她一个小女子,不该有如此雄厚的内力。
心中一面称奇,一面再度发劲,曳出数丈,翻上运河水面,八步赶蝉换为燕子抄水。
不想转身一探,那李细禽仍旧在后坠着,仍旧与他差着半步距离。
紫衣儿暗惊。
那日他只顾着逃窜,没弄明白这小女子的轻功来历,今日看来,她的身法调息定有皆有奥妙,若是在最后半步真被她抢上,自己一世贼王的名号怕真要被踩在地上了。
他左右一看,发现眼下所处乃是运河西岸,前些日子在城中踩点时路过一处芦苇丛,那里极易迷路。
这小丫头一定怕自己半路逃跑。
他四下兜转那么一圈,想着若能用那芦苇丛困住这小丫头一时半刻,赢的把握遂又多了几分。
李细禽见紫衣儿临时转了方向,也不多言,仍旧一路跟着。
那紫衣儿将李细禽引进了芦苇丛,一时四处白茫茫一片,紫衣儿穿梭往来,几乎难辨身影,李细禽倒也不急,环视四方一周,心中已经有了计较,当下发足急掠,再不耽搁,往福缘寺山门奔去。
紫衣儿到时,李细禽正坐在山门下用手扇风,虽说是抄了一条隐秘的近道,但她也确实用上了十成的功力,只是落在紫衣儿眼中,却全然一副等着看他好戏的模样。
紫衣儿本以为自己是甩掉了李细禽,兴冲冲地到了目的地,哪里料到这小女子不知何时已经跑到了自己前面,当即又羞又恼,捏着石灰袋子,心头一小撮火苗左右摇摆。
李细禽看出他似有反悔之意,将手中水葫芦解下来递过去:“前辈渴了吧?这可是上春楼的莲花白,冰过,解渴!”
紫衣儿见她不拿腔调,也不笑他,别别扭扭接了酒葫芦,一口冰酒下肚,心头倒是舒服不少,遂道:“行吧,老头我说话算话,你问吧,若是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李细禽立刻道:“若是我记得不错,九月十五日夜,你应该满城找地方藏身吧?”
“算是吧。怎么了?”
“前辈路过了那片芦苇地?”
紫衣儿想到自己方才是准备使李细禽在那芦苇地里迷路,正是因为那夜他赶上雾天,才在那片芦苇荡里游荡了许久。
“所以,你有看到什么吗?”
紫衣儿面色一惊,“你怎么知道我看到什么了?”
李细禽道:“前辈,此事与本县四起凶杀案有关,我知道前辈虽是扬名江湖的大盗,却从未害人性命,私底下还在磁州开了一个济慈院,是以晚辈才敢与前辈比试脚力,全是因为知晓前辈为人。所以还请前辈据实以告,毕竟人命关天。”
紫衣儿又上下打量她一阵,沉吟一阵,终于道:“你这小女子,倒真是有些不同。罢了,我就将那夜所见说与你吧。”
“前辈请讲。”
“唉……其实你要是不问,我还以为那晚上我是做了个梦呢。”
“梦?”
“不错。”紫衣儿这才缓缓道来,“那夜你们七里堂的人堵住了城门,而我也在城中还有一处秘密之地未曾探过,遂也确实在城中打转。
“等到了这片芦苇地,四周白茫茫的,什么也看不清,我便想要离开,没想到一时迷了方向。
“就在我四处找寻道路之时,忽而听见有人唱歌,雾气之中,若有若无,极为飘渺。
“我紫衣儿在江湖,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什么样的声音没听过,可那个声音,却是我听过最好听的声音。”
“所以你就寻着那声音去了?”
“不错,我寻着那声音,在雾气中走着,不多时就闻到一股极奇异的香气,接着我就看见了一个身高八九尺有余的......哦,不对,那不是人,应该是......”
“鬼怪?”
“不,羽人。”
李细禽万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答案,“羽人?”
“不错,因为我看到那家伙展开了两只足有丈长的翅膀!”
李细禽立刻问:“什么颜色的翅膀?”
“似乎是黑色的,但雾很大,夜又很深,我看得不甚清晰。对了,我还看见那里悬空有一把长剑,再跟着,就有一个人,一步一步向前走,剑就插进了那个人前胸,但他好像不知道痛,仍旧向前在走,直到那把剑直直从他的身体里贯穿。”
紫衣儿描述的场景过于奇异,李细禽一时也有些摸不到头脑,只问:“那歌声呢?前辈可记得唱词是什么?”
“记不太清楚,只是隐约记得巫山女,高唐客什么的,直到那个人一动不动了,歌声才缓缓停下。”
“那你说的那个羽人呢?”
“消失了,一眨眼,就不见了。”
.. ...<未完>
后续精彩内容
可下载“每天读点故事APP”
搜索《姑获楼》 别衡/著
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即刻开启阅读!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每读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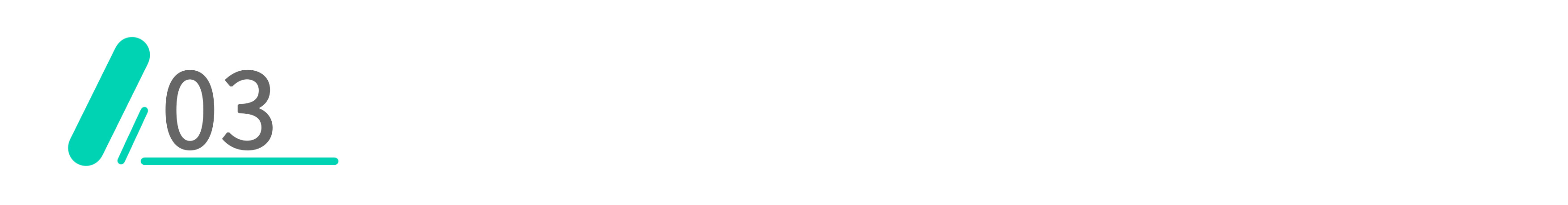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