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写歌的蒙德里安
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是谁?没错,就是那个画格子的荷兰人。
画格子凭什么能去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览,还能卖出上千万美元的价格?背后原因恐怕很复杂,涉及受众心理、市场、艺术流派等等,一篇短文很难讲清。
蒙德里安《百老汇爵士乐》
在我看来,促使蒙德里安成功的重要一点是,他为自己的画找来了音乐这个好“拍档”。
艺术史家贡布里希不是说嘛,在看到蒙德里安的《百老汇爵士乐》(Broadway Boogie-Woogie)之前,他并不知道 Boogie-Woogie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画那些色彩鲜艳的格子之前,蒙德里安曾经是一个安静本分的风景画和静物画家。风车、田野和河流,种种意象都是从 19 世纪荷兰绘画黄金时代中延续下来的,充满了印象主义和海牙学派的味道。
后来,他改名(去掉了原名 Mondriaan 中的一个字母a),搬去巴黎。说到这儿,你已经可以猜到这样的“搬家”意味着什么,想想从西班牙搬去巴黎的米罗和毕加索吧。
蒙德里安《有调味品的静物》
来到花都之后,蒙德里安接触到毕加索等人的立体派主张,并开始了解精神分析学科相关理论。从那两幅创作于同年,但风格迥异的《有调味品的静物》中,我们已能见出画家心态和风格的转变。
这种转变随着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变得愈发鲜明。干脆,《构成》系列之后,蒙德里安完全抛开了以往写实的风格,执着在新造型主义(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用直线和色块画格子)的路上义无反顾了。
等到过了不惑之年,他开始更多地琢磨音乐和造型的关系,画中那些色块和线条,也随著他对爵士乐理解的愈发深入,变得节奏鲜明且富韵律。
他开始只用三原色(红、黄、蓝)作画,就像作曲家用七个音,排列组合成一首复杂曲目;或者厨师只用三种萝卜,做出一道好吃好看的拌三丝。每每看他的画,引我思考的,总是他勾连听觉和视觉经验的尝试。原来,画也是可以听的。
如果,我们执意要为蒙德里安,在中国找一位同道,则不得不提宋末元初的赵孟頫和他的《鹊华秋色图》。这幅元初山水画面中的音乐性,借由笔法、构图以及景深层次,颇为巧妙地传递出来。
《鹊华秋色图》从右至左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包括右段的华不注山以及山前松树,中段的水泽和杂树,以及左段的房舍和远景中的鹊山。
在我看来,这“山—水—山”三段式的排布,与古典音乐中“快—慢—快”的三乐章交响曲颇有几分近似。
画幅中两山首尾呼应,正如第一乐章的主题句,在最末乐章再度出现。而且,画家对于意象的排布,与作曲家处理声部关系时的做法,又似有异曲同工的妙处。
举中段为例,画家将杂树和岩地置于前景,将水泽和长天置于视觉纵深处,总是或多或少引人想及,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慢板乐章。其中漂浮在一片氤氲弦乐上的钢琴声部,宛如赵孟頫画中随风摇曳的草树。
看画若听音这话不假,反过来说,听音如看画的例子,也不鲜见。
嵇康在《琴赋》中提到“状若崇山,又象流波”,是将乐音类比山水浩汤之势;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用银瓶乍破和铁骑突出,来形容琵琶女的琴音,亦生动形象。
每每听到有人感慨,音乐的不可捉摸与无法言传,我总会忍不住说,或兴之所及,许将那些听觉经验,转换为某种视觉经验,也不失为欣赏乐曲的好方法。至少能保证我们妥妥地,在音乐厅的沙发座椅上,捱过两个小时。
其实说到底,哪需要那么多复杂深奥的阐释和读解,不过是听舒伯特的《流浪者幻想曲》时,想象自己在曲折旅途中跋涉;听贝多芬的《欢乐颂》时,想一想天堂的景象罢了。
至于《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那样根据传说或神话改编的曲目,画面性更显得强,单听十八相送和化蝶两段,就足够让我们自动脑补一段古典舞了。
若借用一修辞手法,来形容上面提到的音画关联,大概非“通感”莫属。这个修辞格想必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它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语文考试中,不知出现过多少次。
如今的我,终于从读书时死记硬背的术语中,悟得一二妙处,想来真要感谢赵孟頫,和那个爱写歌的蒙德里安。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美在高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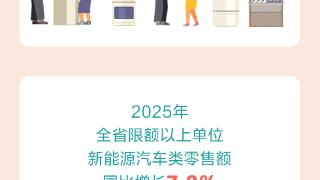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