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月亮的旅行
《穿过月亮的旅行》
截止今天,这部票房不到四千万,是五一档票房最差的一部。
看过之后,似乎又觉得这个结果没那么奇怪了,并不完全是因为质量,它并不能算是那种敷衍的大烂片,更多是因为,这片本身就很难谈得上是市场导向,导演好像自己就没想好这片应该拍给谁看,只是遵从了创作欲望上的冲动,突然喜欢上了迟子建《踏着月光的行板》这部小说,于是非要用自己的方式拍出来。
这种随心所欲,注定了它除了主演张子枫、胡先煦带来的部分流量,受众面很难太广。
这种做法也同时带来了电影的优缺点,由于创作的起点相对纯粹,加上导演并非全无灵气,自然有一些好的地方,让这片能迈过及格线,不至于让人太讨厌。
但也同样因为导演一开始就没想清楚类型定位,改编能力也有限,所以又构成了很多问题,让人很难认为值得推荐。
就我们内部感受而言,整体这片子还是可惜偏多,所以好坏两方面都会聊聊。
正文
好的地方是导演对于年代感和浪漫的部分想法。
先说年代感,电影的主线和原著基本一致,讲的是一个九十年代背景下的爱情故事,一对异地年轻夫妻林秀珊(张子枫饰)和王锐(胡先煦饰)在中秋当天坐火车去见对方,又因为扑空而屡次错过,中间穿插了火车上的世情百态。
从主线就能看出,那个年代里物质生活的局限是这个故事得以成立的基点,也是勾起人们集体回忆的锚点。
虽然电影里很多相关情节都依赖于原著文本,但你也完全能看出导演的用心与巧思,他用了许多的描写和细节来加以落实,譬如两个人每次坐错都要经历重新排队买票,等车,中间也没有电话或手机可以即时沟通,到了地方去找人都得挨个问。
譬如当时治安没那么好,逃票时有发生,打架是性子一急就会动手。
像王锐想要买盒饭那一段也满是易于共鸣的细节,乘务员推着车喊着“腿收一收”,慢慢地过来,无法因为王锐提出想吃而加快速度;王锐听闻盒饭价格的犹豫与不满,也很写实。
除了表象的年代感,对九十年代那种内含生命力的社会氛围,电影也复原得比较好。
这从夫妻性方面的需求便能看出,他们每次见面第一件事都是找旅馆上床,这不仅符合异地恋恋人心理,也更有一种蓬勃生机蕴含其中,他们对欲望是不否认的。
车上众生也是整体向上、带有希望的基调,从带着月饼去见客户的小老板,到为了寻找理想生活的出轨的女人,再到钱包里有几十注彩票的股民,他们都各怀其梦。
另一个是对浪漫的处理,导演知道浪漫应当是现实与想象的结合,人心与外物缺一不可,有些桥段也确实是生效了的。
就说我最喜欢的一个设计吧,开头埋了一个伏笔,是站台上的保洁员,正在用胶带把自己开口的破鞋子缠起来,好能够继续穿。
电影最后一个镜头把这个伏笔收了回去,这个保洁员捡到了王锐因为赶火车而丢弃在站台上的鞋子,老人穿起来刚好合脚。
这样的浪漫是以现实的困苦来对应完成的,美感和悲剧性达成了统一。
可惜的是,导演没有办法将这种浪漫进行全局意义的贯彻,在改编上还是缺乏想象力,于是除了零星的设计有效,最终效果是现实与浪漫相互错位,各自独立,两边都不着靠。
电影里大部分的浪漫是没有根基的,是虚无缥缈很难找到共鸣点的,就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来说,林秀珊听说对面坐着的是死刑犯人,会吹口琴,毫不犹豫就劝说刑警让他吹,而且引来了全车底层劳动人民的围观,欣赏,最后还哭成一片。
这种所谓的浪漫已经超出了当时人们需求与追求的普遍范畴。
类似于两个人毫无约定就能在电话亭接到对方电话,以及王锐因为又撞到乘务员,没钱补票而不得已下车,成功跟林秀珊见面这种种依赖巧合的浪漫,也就不用展开说了,全都跟现实挂不上钩,显得非常儿戏。
现实这方面也没做好,从美学风格可见,导演倾向于浪漫的超现实写法,这本身也不算什么问题,像韦斯·安德森的电影就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形式与内容彼此和谐,互相作用,内核还是现实向的讨论。
但《月亮》不是,它只有表皮,没办法服务于内核,进行完整的表达。
所以连人物都像是迁就于视觉的产物,在这个如此需要人物和表演来支撑的故事里,演员们表演虽然没问题,人物设计和选角却不匹配。
原著里的男女主以及彼此的错过,之所以比较可信和感人,是因为你从作者描写就能感觉到,他们从形象到处境都透着一种无产阶级共通的匮乏、贫瘠与疲惫。
迟子建特意写了女主的牙齿“黄黄的”,能吓退一些求爱者,而且她并不在意,反而颇为自得,这反映的就是小市民阶层的物质局限和认知局限。
这让他们偶然的见面就像漫长黑暗里的光,他们都渴求彼此的陪伴和抚慰,在他们的观念里彼此就是唯一,所以这一天的来回,或者说每一次来回都显得格外重要,甚至必须。
但电影里,或许就是因为审美风格的需求,两位演员的形象和气质都透着一种精致,以及偏年轻的稚气,有着与身份不相称的离地感,让整件事看上去更像是小孩之间的嬉闹。
就说张子枫演的林秀珊吧,从她上车第一幕你就能感觉到,她跟周围那些抱着包袱,各怀心事的大爷大妈是不一样的,她脸上没有任何被生活欺辱过的痕迹,眼神里也透着一种清澈的明亮,对发生的任何事都不是报以司空见惯的沉默,而是好奇和期许。王锐也差不太多。
并不是说这样的新婚夫妻不可能存在,但对于这样的故事而言,这样的人物的确令人难以信任。
你会忍不住想质疑,想推翻原著里原本的深情设定,想问你们见这一面有那么重要吗?你们看上去根本没什么经济压力和生活苦恼,到底为什么会愿意忍受这样的来回颠簸和辛苦呢?
不仅人物上缺乏支撑,回忆线和当前线的比重也分配失衡。
很多当前交往的细节被省略了,占据大篇幅的是从前那些跟口琴和牛相关的所谓浪漫片段,比如王锐怎么让牛给林秀珊转圈,怎么为了林秀珊拒绝相亲,带着假炸药去恐吓拐走了自己牛的相亲对象父母。
这让他们的情感关系少了很多层次,对话很少,甚至都没一起吃过一顿饭,基本都是在旅馆度过,似乎只呈现了爱的结果,没有爱的过程,让观众难免少了些代入感,进一步削减了信服力。
除了改编功夫不足,还有一些陈旧性别观念的间隙流露,未必是有意的,但确实带来了一些不适。
王锐本来想给妻子买裙子,却因为怕妻子“被坏男人盯上”而买了玫瑰花,目的是让妻子拿去炫耀,甚至自己也拿了在门卫前炫耀,最后还跟妻子直说了,而原著里男主在纠结之下只是默默换了个花色,还是选择买布给妻子做裙子。
两相对比,电影自我感动的意味更重,所谓浪漫也必然打了折扣。
还有火车上那个出轨后跟丈夫回家的女人,电影也多给她加了一句“我回家过中秋”的台词,强调了她的选择和心意,非常多余。
包括原著里原本有的一些落后陈述也照本宣科,林秀珊为了表明自己跟死囚犯不认识,跟刑警说“我是王锐的人”,这样的表达虽然能理解为当时人物的局限性,但导演没有从任何地方进行反驳或改动,让这种纯爱带着一些迂腐和不应时的气味。
如此,这片从票房到口碑也只能落个尴尬位置了。
音乐/
配图/《穿过月亮的旅行》预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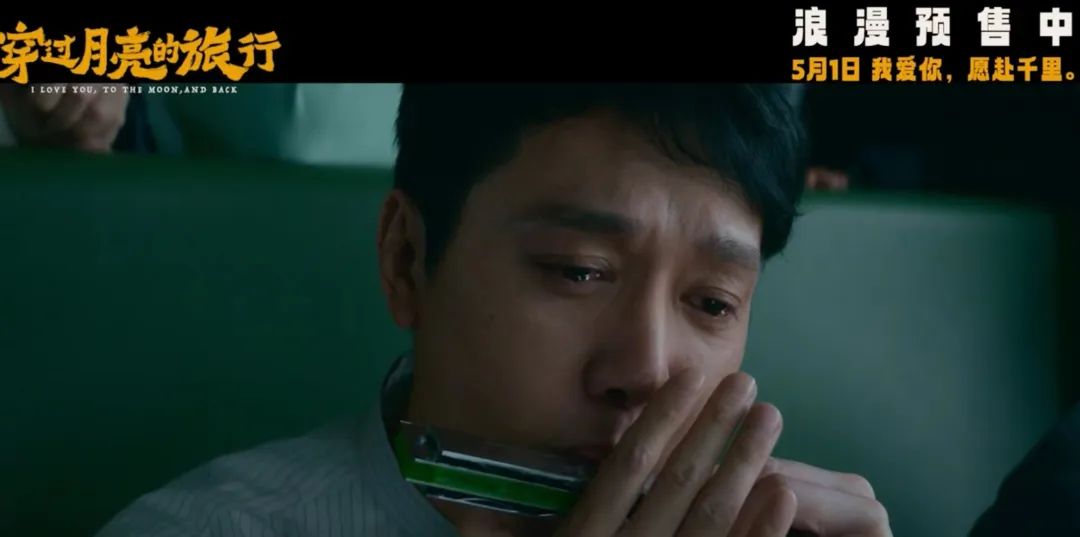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