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陪伴当爱,他把我当妹妹
八年前,我和许砚告白。
他跟我说:“你只是把陪伴当作了爱情。”
八年后,当我身侧已有旁人,他却问我。
“给我一个机会,我们试试,好吗?”
我和余北分手的第十天,时隔八年,我再一次见到了许砚。
平市初冬下起大雨,我在酒店宴会厅参加完好友的订婚宴。
踉踉跄跄走到大堂,推开想搀扶我的司机,说酒店的香薰熏得我头疼,自己想出去透透气。
帮好友挡酒太多,以至于我呼吸到室外冬雨带来的冷空气,看见许砚的那一刻,我以为自己是真的喝醉了。
许砚撑着一把伞走到我面前,隔着半米距离,我敏锐的嗅觉甚至能捕捉到潮湿空气中独属许砚的气息。
我不敢呼吸,甚至不敢眨眼,只觉得许砚是我醉后出现的海市蜃楼。
但当他叫我名字的那一刻,我却像一只陷入险境的兽类,四肢血液冻僵,完全无法动弹。
“颜心。”
我努力让自己的呼吸频率显得正常,顿了一会,才能勉强用寻常语气开口:“好巧,竟然在这儿碰上,你回来出差吗?”
时间仿佛对许砚格外偏爱,他没有变胖变圆变成大叔,而是如我模糊记忆中一样英俊。
八年光阴只给他的外貌赋予了美好的东西,他比以前看起来更成熟,更沉稳,更可靠。
他默认了我问他是否出差的问题,问我:“喝了很多酒吗?我送你回去。”
我是喝了很多酒,酒精也让我的头和胃隐隐作痛,但我的思绪早在我看到许砚的那一刻清明无比。
我摇了摇头,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笑,往后稍稍退了一步,不着痕迹避开他要扶住我的手:“不用了,家里司机在等我了。”
许砚动作僵了僵,手悬在半空,最后又放下,看了我一会,在我准备上车前问我:“能把我从通讯录黑名单里放出来吗?”
我没想到他会说这句话,愣了愣,说:“你不在我通讯录黑名单里。”
说完我把手机软件打开,给他看空空如也的黑名单界面。
他眼光在我手机屏幕上流转,眼底是我看不懂的情绪,低声说:“没看到你朋友圈,还以为你把我拉黑了。”
我摇头,说怎么会,又说大概是分组的时候忘记把他放进去了。
关上车门前,我听许砚说:“那我过两天找你吃饭。”
“好吗?”他问。
我努力笑了笑,点头说可以,又和他道别,让司机出发。
雨幕中后视镜逐渐看不清许砚的身影,我才发觉自己掌心被指甲掐出几道深深的印子,后知后觉的疼痛提醒我,这不是场梦境。
我当然会礼貌和许砚打交道,毕竟我们又不是仇人,也不是有感情纠纷的前任男女友,只是普普通通的旧相识。
车子驶回家中,母亲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见我回来,抓着我聊天:“下午许砚来了。”
我愣了一下,她指着茶几旁的几盒礼物说:“许砚啊,以前住咱们隔壁那个许砚。隔了几年越来越稳重了。”
我下意识透过家中落地窗望向隔壁栋楼房,但那栋屋子的灯光一如既往没有亮起,依旧无人居住。
妈妈问我:“他回来你不知道吗?你们没有联系吗?”
我摇摇头,说没有。
她小声说了一句:“我记得你们小时候关系挺好的。”
我扶着楼梯把手缓缓上楼,听闻这话,垂了垂眸,说:“那也只是小时候的事了。”
许砚一家,是在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搬到了我们隔壁。
他和我哥哥年龄相仿,我哥哥外向爱玩,呼朋唤友,而许砚性格好,少年的友情纯粹简单,很快打成一片,时间久了,自然水到渠成地关系很好。
许砚父母工作忙,于是他成为我们家常客。
那时我偶尔会跑到高中部找我哥,有一回迷迷糊糊走错楼层,走到许砚班级门口。
许砚和同学拿着篮球,在走廊碰上我,把我拦住,温声细语:“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疑惑看了一眼楼梯标识,恍然大悟,说自己走错了地方。
篮球队同学问他:“许砚,这个小朋友是谁啊?”
许砚笑笑,顺手呼噜了一下我的头:“是我妹妹。”
后来两年,我会坐在篮球场边,拿着两瓶水,指着场上身影,说:“那是我哥哥,哦,那也是我哥哥。”
我的审美观大概是在我哥和许砚的荼毒下定了型,也懵懂地明白他们受欢迎的原因。
他们总是把简单的校服穿得好看,在球场阳光下灼灼生辉,闲暇聊天时笑容灿烂大方,坐在窗台边看书时清冽安静。
这种出场如携带一层虚虚光圈的男生,承载了女生们酸涩甜蜜的怦然心动和情窦初开,为旁人在暗淡无光的学生时代留下记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无疾而终的青春时代的代名词。
我也喜欢许砚的模样,如同喜欢一套乐高,喜欢一艘船,喜欢一个景点那种喜欢。
他们在学校受欢迎,连带着我都能收获漂亮姐姐们的巧克力饼干投放。
漂亮姐姐们会围着我,和我讨论我这两个哥哥的喜好,一般这种时候,我亲哥会吊儿郎当出现,说:“颜心,别啃零食了,待会回家吃不下饭,小心长不高。”
而许砚会把我从人群中提溜出来,客客气气和人道:“不能再给她喂东西了,今天甜食摄入超标了。走啦心心,回家了。”
记忆中许砚从少年时期就做事仔细,为人体贴,性格靠谱。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许砚比我亲哥更像亲哥。
我很多处事和技能都是许砚教的,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许砚。
曾和他拿着桨板学会冲浪,手脚并用学会攀岩。
也在困顿时分听他讲解过几何模型,容他手把手教会我计算物理题目。
有一年我们去攀爬一座雪山,下山时我被山体陡峭吓住,迟迟不敢往下走。
他站在距我一两米的位置,说:“别怕,我接着你,顶多我给你垫着。”
我犹疑许久,终于迈出脚步,于是果然喜提踩空,可是许砚接住了我。
他用了很大力气,才不让我们俩双双摔倒在地,抓着我的手,笑着和我说:“你看,没摔。”
许砚仿佛是我的机器猫,永远能解决我的难题,我问他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许砚,这个怎么办呀?”
物理学中说惯性定律,我想我对许砚的依赖才是一种惯性。但惯性是有危害的,只是年少的我从未意识到这一点。
许砚说约我吃饭,不是嘴上客套客套。
隔日他就出现在我工作室楼下,问我想吃什么,又递给我一包糖炒栗子,说来的路上看到了,就顺手买了。
我没有告诉他我已经戒掉甜食,只是把糖炒栗子放在一旁,一粒也没有剥。
我想我比年少时更有出息,至少能够和他如故交般,在餐桌上游刃有余地闲聊,好似真是久别重逢的好友,简简单单吃个晚餐。
吃过晚餐后,他说他要送我回去,却被我拒绝:“我开了车来。”
不曾想他却点头,说:“那也好,要不你送我回去吧。”
其实对上许砚,我几乎讲不出任何拒绝的话,甚至我身体里的惯性因子又被调动起来,把刻意遗忘的细枝末节都回忆得清楚。
平市的夜晚依旧热闹,入了夜主干道依旧熙熙攘攘,车子融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中,许砚侧首,忽而说:“你现在车技很好。”
“也还好。”
我不由得想起,我刚成年时拿到驾驶证上路,身侧坐的也是许砚。
那天他同样坐在副驾上,看我慢吞吞发动了车子,我胆子不大,在很宽敞的马路上,也只敢开二十码,甚至被一旁骑自行车的路人超过。
许砚没有不耐烦,和我说别怕,说他扶着手刹,随时帮我刹车。
但直到他离开之前,我都没有真正学会驾驶车辆。
“这些年,有人教你吗?”许砚看我娴熟地超了几辆车,问。
我摇了摇头,轻松道:“没有。其实很多事情,学着学着就会了,你看我这个摄影工作,每年都要自驾出门采景,熟能生巧。自从在冰岛抛锚一次,我现在连修车都会了。”
透过后视镜,我看到他很轻地皱了皱眉,问我:“抛锚?余北没陪着你去吗?”
车子停在许砚入住的酒店公寓楼下,我侧首看他,轻声说:“那时候,我还没和余北在一起。”
许砚顿了一下,问我:“怎么抛锚的。”
我把眼光移开,很慢地叙述:“是前几年的冬天,我一个人去采景。那时没什么野外经验,以为有钉胎就没事,结果还是车技不佳,车子在冰面上打滑,抛了锚。
“恰好那里方圆十里毫无人烟,也没信号,而车子油量不多,我险些以为自己要冻死在冰川下。”
他声音有点哑:“然后呢?”
“所幸后来等了两三个小时,等到了一辆路过的车子,车主帮我将车从冰面拉上来,又协助我打了道路救援电话。”
我语气轻快:“那趟旅程后,我马上给自己报了一个修车课程,现在抡起千斤顶来,怕是比你们都熟练。”
可是许砚听完没有觉得有趣,也没有任何言语。
而我笑了笑,垂下眸子,说:“所以有没有余北又怎么样。你看,没有别人,我一个人也能解决这些问题。”
说的是余北,但其实话是讲给许砚听的。
我觉得许砚是我心口一块疮疤,结了痂,谁都以为好了,可是当他重新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轻轻一触伤口,才发现里面依旧鲜血淋淋,尚未愈合,只是一直都被刻意忽视。
你看,没有你又怎么样呢,在没有你的日子里,我还是学会了各种技能,而在你不知道的困境中,我自己也能解决所有棘手的问题。
谁离了谁都活得下去的,谁又不是非谁不可。
在许砚面前揭开心头伤口让我痛不欲生,可我却还要硬生生把它摊开来给他看,所以终究把气氛搞得僵冷,我下了逐客令:“你到酒店了,晚安。”
我忘记我是什么时候习得“喜欢”的真正定义,但能肯定的是,我是在许砚身上体会到心动的感觉。
有一段时间,家里装了家庭影院,恰逢我哥酷爱看恐怖片,常常邀约一众好友到家中观影,而我又菜又爱玩,明明胆子小到不行,还非要跟着看。
一群人周末在我家观影房,关了灯开始看《山村老尸》《咒怨》《午夜凶铃》,翻来覆去那几部片,但不管第几次看,我都会躲在一堆抱枕中瑟瑟发抖,在贞子出现的时候胆战心惊。
我哥无情地开我玩笑:“颜心,看你比看恐怖片有意思多了。”
许砚比我哥有风度得多,不仅不嘲笑我,还会陪我坐在观影房最角落的位置,一有惊悚画面,就抬手挡住我眼睛。
他说:“没事,不怕。”
他那时已经很高大,手指骨节分明,手掌宽敞温热,让人觉得很安心。
我抓着他的手,蜷在他旁边,透过他手指指缝偷偷看观影屏幕,鼻息间尽是被他身上干净的气息包裹,也觉得没那么恐惧了。
十六岁那年的冬天,受多重拉尼娜气候影响,平市很早就降了温,初冬就落了几场大雪。
而每年雪季都驰骋雪场的我,却在寒假时节做了个小手术,被父母关在家里休养生息。
父母家人一贯纵容我,但到身体健康问题上,却寸步不让,生怕我出了门受寒受冻,别说是雪场,就连家门都不给我踏出半步,每天按着我待在暖气氤氲的室内,一盅又一盅喝滋补汤药。
我拿着手机里的景点宣传画报和家人比划,撒娇打滚,说自己真的非常非常想去圣诞雪镇玩,又连连保证自己会穿得很多很多。
然而并没有获得豁免出狱权,甚至家人生怕我半夜跑去阳台玩雪,还在我房间的阳台门上加了一把锁。
我惨痛地望向我家编外成员许砚,寄希望于他能和我一起举旗造反,不想他也严肃地点头表示赞同。
一群人恨不得拿个玻璃罩子把我罩起来,放到温室里养着。
平安夜那晚,我躺在房间床上,关了灯,百无聊赖拿着手机,看着雪场圣诞活动图片唉声叹气。
忽而阳台玻璃门被敲了敲,我吓了一跳,起初以为是幻听,但敲打玻璃声却没停下。
我按亮了阳台昏黄的小灯,拉开窗帘,就看到许砚站在外头。
我想我那一刻的表情大概只能用目瞪口呆来形容,张了张嘴,第一句就是问他:“你怎么在这?”
但我很快意识到玻璃门的隔音太好,许砚根本听不到。
他笑了一下,扬了扬手上的手机,示意我接电话。
“过来给你送圣诞礼物。”他声音从听筒传来。
“你怎么上来的?”通往阳台的唯一通道就是我房间,而且此时还被上了锁。
“从我家攀过来。”他抬手指了指,指给我看,说他家二楼的书房阳台和我房间挨得很近,他从那头偷偷摸摸爬过来,身上冲锋衣还有一些灰白色痕迹和未干的雪水。
“什么礼物还得爬墙送呀。”隔着玻璃门,我和他对视。
许砚笑笑,往旁边走了一步,露出被他挡在身后的露台小桌。
小桌上堆了个半臂高的雪人,头顶还放了个小小的圣诞帽,橘黄色小廊灯让雪人身上染了淡淡的光,许砚声音很低,说:“心心,圣诞快乐,不要因为没得出去玩不高兴了。”
雪势不算很大,如同满天绒花絮絮坠下,把室外的许砚衬得像赠梦的神使。
他棱角分明的面容在灯光下显得柔和,青年的稳重和少年的阳光交织在一起,眼底有浓郁的笑意。
而我的指尖触碰玻璃门,感受冰凉温度从指尖传到手肘,但慢慢又变温变热,如同我心底将近溢出来的喜欢:“我没有不高兴。
“我很喜欢的。”
许砚和我在电话里随意聊了一会,最后又攀着阳台栏杆,翻回他家去。
爬树爬墙这种不体面的事,完全不像是许砚这种人会干出来的,但他做这些动作时,连姿态都显得得体。
他的身影消失在阳台,留我一个人站在原地发怔。
过了一阵,他又拨了一个电话给我,和我说:“好好养身体,以后还有很多个冬天。”
我望着室外那个昏黄灯光下的雪人,很轻地“嗯”了一声。
十六岁那年的圣诞,二十岁的许砚,在我人生所有的际遇和心动中,轻而易举拔得了头筹。
我曾以为我一定会和许砚在一起。
读高中时的一年情人节,许砚到学校接我下课,他从教室后门绕进去的时候,我桌上堆满了各式礼物。
许砚在我身后拍了拍我的肩,欲盖弥彰说:“这么多巧克力呀?”
我转身看他,笑眯眯道:“哪有以前你收得多。”
他一副家长的语气,甚是不满:“他们送给你你就收了?长这么大了,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爱吃甜食,这么容易就被人收买。”
我面上装作一副苦恼的样子:“你生什么气呀?他们直接放在我桌上的呀,我又不能丢掉。”
许砚随意翻了翻,又把巧克力里边的情书通通没收,如同下达命令一样给我建议:“那就分给同学。”
他帮我甜品大派送,却被我拦住,我从桌上的礼物里抽出一盒曲奇,说:“这盒不行。”
他脸色瞬间变得严肃一些,站在我跟前,居高临下问:“为什么这盒不行?”
又连连拷问:“这是谁送的,你才多大就谈恋爱?”
我将曲奇包装拆开,自顾自啃了一块,才说:“这是我自己买的呀,你吃不吃啊?”
他表情变得缓和一些,勉为其难拿了一块饼干,又说教我不能早恋。
我仰着头望他:“那哥哥,我要几岁才可以谈恋爱呀?”
许砚拿着餐巾纸拭去我脸上的饼干碎屑,动作很轻和,又把我怀里的曲奇盒子抽走:“等你长大一点儿。”
后来我长大一点儿了,考上和他一样的学校,在十八岁的圣诞,和他相约去札幌看我心心念念的雪灯。
他一如既往说“好”,声音也一贯地温和:“你喜欢看什么我都跟你去看。”
但后来我们没在雪季抵达札幌,因为在临行出发的前一天,许砚告诉我,他要爽约了,不能陪我去旅行了。
他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站在路灯下,语气有些低沉,和我说“抱歉”。
彼时的我很善解人意地说没关系,又自然而然挽他的手,说:“反正每年都有得看呀。”
那年平市没有下雪,而我做了人生最错误的一个决定,便是忽而头脑发热,踮起脚吻了许砚的侧脸,说:“没关系,我那么喜欢你,我们明年再去也行。”
许砚怔住,好似僵了半分钟,才慢慢把手从我怀中抽出来。
他看了我很久,眼底情绪翻涌,斟酌犹豫如何开口,最后躲开我的眼光,和我说:“心心,我很喜欢你,是像你朋友和哥哥那样喜欢你,而不是男女之间的喜欢。
“你年纪还小,只是把陪伴和亲情误以为是爱情。”
他说他马上要赴海外求学,也许往后一些时间,我多接触新的同学新的朋友,会发现我和他并不是男女之爱。
那是我和许砚最后一次见面,往后的八年,我们再也没有一条短信的往来。
对许砚的喜欢如同一场高烧,让我产生幻觉也让我体验痛意。
所以病好之后,有关“许砚”的记忆,就被我硬生生封存在脑海一角,如果不刻意想起,其实我会偶尔忘了这个人的存在。
许砚开始频繁出现在我工作室附近。
起初一两次还能用巧合来解释,出现的频率多了,倒显得刻意了。
在不知道第几次吃饭时,他说:“嗯,刚好分公司开在附近。”
我低头吃饭,没深究他话中的真假,也没阻止他给我们工作室带下午茶的举动。
年底时我有场重要的慈善展览和拍卖会,几近忙得脚不沾地,即便没有刻意躲着许砚,见面也见得少得多。
展览快结束的时候,余北出现了。
我俩两个多月没见面,这次见面的时候他拄着拐杖,一瘸一蹦跳到我跟前,倒是很喜感。
外界传得沸沸扬扬,说余北和我分手后,余老爷子大发雷霆,对自己家里出了个渣男深恶痛绝,于是家法伺候,把余北揍得进医院躺了大半月。
余北看上去像是来给我赔礼道歉似的,十分有诚意地斥巨资拍下我两幅作品,又狗腿地问我要不要一起吃个宵夜。
他问我这话的时候,我一转头,看到许砚站在离我两三米远的地方。
许砚不由分说走上前来,站得离我很近,突破了安全社交距离,好似幼时那样亲密无间,手臂微微环着我,掌心扣着我的小臂,问我:“工作结束了吗?我送你回去吧。”
他表情没有不满,但浑身气压却莫名很低,语气却有点生硬,有种执着让我一定要二选一的意味。
余北自幼和我们生活在一个街区,和我也算青梅竹马,自然认得我和许砚。他眼光在我和许砚身上流转,扑闪着他那狗狗桃花眼看我。
我很轻地叹了口气,和余北说“回见”,终归和许砚上了车。
平市下起小雪来,车内连电台都没开,车子开行十来分钟,许砚突然问我:“你是怎么和余北在一起的?”
“怎么突然问这个?”
他说:“我想知道。”
我看着眼前小雪,语速很慢,陷入一点回忆中去:“有一年半夜,突发急性阑尾炎,自己叫了120去医院。我没和家里说,怕家里担心。”
“但我那个时候凌晨躺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我想我是需要有人陪着的,而余北恰好来陪我了。”
许砚握着方向盘的手收紧,手背上青筋嶙峋,但他语气却很平和:“那为什么又分手了?”
我笑笑,这问题太简单,我早就和人重复过千百遍:“不合适就分手了,哪有那么多理由。”
“那你还为他买醉?”
我愣了一下,忽而意会到他是有所误会,想解释我们刚重逢那天我只是替人挡酒,话到嘴边却又被我咽回去。
我沉默很久,最后说:“那也没什么,困难会过去,生病会过去,失恋的阵痛会过去,喜欢一个人的感觉也会过去,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车子停在我的公寓楼下,我下车准备上楼,许砚却也跟着下车,不紧不慢走在我身后,仿佛是要送我。
我站在电梯门前,说:“许砚,你当年说得对,人只要往前走往前看,就不会在乎身后曾经有过的风景了。”
我意有所指:“所以许砚,就送到这吧。”
说完我便上了楼,没敢再去看许砚面上的表情。
屋内一片昏暗,我站在阳台边往下望,许砚车子还停在楼下。
我没再多看,开了灯,查阅了明天的飞行航班,开始收拾行李。
约莫拾掇了二十分钟,我最终还是想知道许砚走了没有,又走到温度零下的阳台。
黑色车子依旧没动,停在原地,车顶积了一层薄白,我等了一会儿,也没等到许砚出现。
我不明白他能在楼下做什么,突然觉得很生气,连外套也没披就下了楼,一出有暖气供给的大堂,就看见他背对着我倚在墙边,站在没什么灯光的阴影里,边抽烟边咳了两声。
“许砚。”我叫他。
他听见我声音,迅速把烟掐灭了,动作娴熟,一看就是老手。
“怎么穿这么少就下楼,外面冷。”
他浑身笼绕着烟味,掐了烟也没办法迅速散去。
我看他依旧是下车时单薄的穿着,还准备将身上仅剩的外套脱下来给我,想说难道你就穿得不少吗,难道你就不会冷吗?
和许砚重逢以来,三天两头的见面让我恍惚觉得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我没有一刻像此时这样,如此鲜明地意识到原来我们已经分别了八年。
八年间他未曾看见我病痛、困惑、拿奖、得意,不知道我为什么变得和他一样说话滴水不漏。正如我没有见过他成功、稳重、失意、落寞,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会的抽烟。
错过的时间就是错过了,没有交集就是没有交集,我们失去默契,摸不清对方心思,说出每一句话前都要再三思索是否妥当。
我问他:“你在这儿做什么?”
他深深看了我一眼,好像是在下什么决定,然后说:“想和你在一起,想离你近一点,在想怎么追你。”
我愣了一下,话倒是脱口而出:“方法是在楼下挨冻吗?”
说完我们都沉默了,许是在室外久了,他又咳了两声。
但苦肉计对我来说没有用,我甩手就准备回公寓去。
走了几步回头看,见他站在原地,我没好气地问:“你还站在那儿干嘛,是打算在这儿冻死吗?”
他听懂我的言外之意,马上就跟在我旁边。
在电梯里,他突然说:“那挨冻有用吗?可以在你这儿排上队吗?”
这种小心翼翼而试探的语气从他口中说出来,让我顿时眼眶发酸发痛。
我脸色不太好看,冷嘲热讽:“挨冻有用的话追我的人都在楼下当冰雕算了,按你这么说,我还不如在我家门口装个打卡机,每天积分考勤打卡,时间一到选分数最高的那个人。”
但他好像当了真,问:“真的吗?”
说罢拿着他自己手机搜索,又问我:“要买指纹打卡仪还是人脸识别的?”
我一把抢过他手机,看到他屏幕界面真是在购物软件的下单界面,气不打一处来,问他:“你是有病吗?”
他又噤了声。
屋内暖气让我血液回暖,许砚看了看我散落一地的衣服,问我:“你这是要去哪?”
我烦躁地将东西乱糟糟塞进箱子:“我明天去札幌参加雪灯祭,去拍照。”
说完这话我就后悔了,因为我们从前未完成的旅程,就是要去看雪灯。
而后我听到许砚问我:“那我跟你一起去,可以吗?”
“心心,给我一个机会,我们试试,好吗?”
直到飞机落地在机场,我都觉得有些恍惚。
飞行间隙时我昏沉睡去,有熟悉的气息将我包裹,醒来时我靠在许砚肩头,而他半拥着我,仿佛一对亲密无间的伴侣。
抵达札幌的前几日,我陆陆续续参加了几个友人的展览。
每每我忙工作,坐在桌边翻阅我一整日下来单反里的照片时,许砚也埋头审阅公司文件,他做出这样一个突然性的决定,如私奔般和我私逃到天涯海角,自然堆积不少公司事务。
我当然知道公司离不开他,这些年他把公司做得越来越大,从澳洲做到北美,新闻报道说他年轻有为干劲十足,怎么可能是闲人一个。
但和我出门时,他却一个工作电话都不接,永远跟在我身后拎设备,又去牵我的手,揽我的肩。
我没有推开。
只因为这个人是许砚而已。
札幌之旅的第八天,晚间我接到一个重要编辑的来电,要我发送一组图片。
我和许砚说:“我借一下你笔记本发邮件。”
他还在开一个电话会议,拿着笔给我写了个密码,又指了指桌上的笔电。
我很快写完邮件,又习惯性登录一个照片网站,想将自己的新作品上传上去。
却是在输入网址后,看到了那个网站上已经有默认的登陆账号和密码,账户名写着“anonymous”(匿名者)。
我陡然意识到了什么,一瞬间想起近几年,每年年末的慈善拍卖会上,总会有一个匿名人士拍下我的压轴作品。
慈善晚宴的最终目的是捐助,但这个匿名人士却从未透露姓名,我们曾猜想他或许是个良心不安的奸商,所以偷偷用“anonymous”这个名字坚持不懈拍下作品,用公益捐赠去补偿自己的良心。
但此时我却好像发现自己的思路错了,因为我触碰到了这个匿名人士面具下的真容。
我点击了登录,看到了这个账号曾经拍下的那些作品——
我岌岌无名时,很多张不值钱的作品,以及我如今奖项在握,每年慈善晚宴的压轴之作。
我在那一瞬间头脑空白,血液结冰,盯着账号的记录,天灵盖嗡嗡作响。
我想我应该有点隐私道德观念,不应该再往下看了,但我没办法自制,不受控地打开电脑文件夹,去翻阅许砚笔记本里的私藏。
冥冥中我觉得,或许会有关于我的东西。
他的文件归属和他的性格一样有条不紊,我几乎不用费太大力气,就找到自己的照片。
那些我在朋友圈发布,却刻意屏蔽许砚的照片。
还有一些和友人的合照,大概是许砚从我们共同好友处看到,又悉数保存到本地。
女人的第六感在此刻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不仅将他电脑文件翻了一遍,又抽丝剥茧,去看他的浏览器搜索记录。
在近三个月的浏览记录中,我看到了他曾输入的搜索关键词。
“智能化打卡机如何安装”
“冰岛冬季危险性”
“颜心摄影”
“慈善展览颜心”
几行冰冷的搜索记录,却让我呼吸困难,喘不过气。
原来在我无数个深夜辗转难眠,往搜索引擎输入“许砚”这个名字,输入他公司名字,看有关于他的每一篇报道的时候,许砚也在网页新闻的只言片语中,寻找有关我的一点消息。
正值此时妈妈发来语音,和我说:“心心,今天许伯父和许太太来家里做客了呢。”
“我听许太太讲你许伯父近几年的大大小小手术,听得心惊胆战,心心呀,你别总是熬夜,我跟你讲,身体是革命的唯一本钱。”
我难得没嗯嗯啊啊敷衍妈妈,愣了一下,发信息问:“什么手术?”
“心脏手术。”
好像所有迷雾中的未知思绪有了一点头目,我问:“第一次做手术,是什么时候?”
我打字的手有点颤抖:“妈妈,你问问许伯父,问清楚些,这对我很重要。”
过了好一会,手机传来新消息。
“七八年前的手术了,不要担心,现在许伯伯都恢复得很好了。”
这一夜,我又一次浏览了有关许砚的各式报道。
其实每一篇新闻我都看过很多次,全部新闻的链接被我放在一个收藏夹里,我一篇篇点开,又一次看许砚的发家史。
他接手公司的时候,他家公司还只是个中流制造企业。
在他手上,企业扛过罢工潮,经历过行业冷淡期,和竞争对手打过价格战,曾接近破产边缘而起死回生,也曾与股东反目而对峙法庭。
但媒体十足偏爱许砚,或许是由于他的外貌,也或许是由于他出色的演讲能力,他们形容许砚是行业的领军者,是一个新锐而眼光独到的掌舵人,他快速扩张市场份额,带领团队在商业浪潮的起起伏伏中披荆斩棘,将一个家族企业做成跨国公司。
记者酷爱夸大成就,在许砚功成名就,站在顶端时,轻描淡写般一笔带过公司上升道路上的坎坷。
但我忽而意识到,当年他接手公司,扛住父亲病重压力,抵御对家们虎视眈眈的时候,他也才22岁。
22岁的他究竟是怎么驯服那些老狐狸的,是怎么在医院和公司间来回奔波不疲惫的,又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把我推开,和我说“我们之间不是喜欢”的。
熬夜的后遗症果然是次日两眼发肿,许砚和酒店客服要了两个冰袋给我敷眼睛,才稍稍缓和一些。
我们启程去会场看雪灯祭的时候,许砚在给我提供晚餐餐厅的选择。
他报了几个餐厅名字,我突然打断他,问:“你为什么买我的作品?”
他愣了一下,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你都知道了啊。”
我点头,他说:“想买就买了。”
“那为什么还要匿名拍下?”
他扯出一个笑,但笑不到眼底,看起来倒有点像苦笑,犹豫半晌,习惯性摸了摸口袋,好像有点想下车去抽根烟逃避这个问题的冲动。
他沉默很久,说:“怕你知道是我,你会不高兴。”
“我高不高兴很重要吗?”我问。
他点头:“当然重要,只要你高兴就足够了。”
他继续那个晚餐话题,说:“你不是一直想尝这个师傅的手作吗?我订了张台,看完灯我们可以去吃。”
他总是这样,事事考虑周全,永远以我的喜好为先,恨不得把我面前所有阻碍所有困难都按他的想法扫平。
“那我如果觉得和你在一起不高兴呢?”我突兀说,“你说试试,我们也试了几天,但许砚,我觉得我们过去了,还是算了吧。”
他好似没听到我说话,只是看上去浑身肌肉紧绷,还在继续往下讲:“他们说今天有新鲜的海胆,你应该会喜欢。”
我重复了一遍:“许砚,我说,我们还是算了吧。”
他噤了声,我第一次在他面上看出无措,良久,他说:“这才几天,要不还是再试试吧。”
我摇头,看他逐渐灰败的神色,觉得心如刀割,却说:“不了吧,再试也是这样的,错过的时间就是错过了。”
却被他一把抓住手,他问:“错过的我都补给你,好不好?你想要什么,都从我这儿拿,我一样一样补给你,好不好?”
手腕被他扣得很痛,但远不及心里的钝痛,我咬咬牙,说:“如果我不想从你这儿拿呢?你不是说我高兴是最重要的吗,我可能打算和余北复合了。”
他面容灰败下去,连嘴唇都带着有些颤抖,却一直沉默。
车内歌曲循环完一首,我问他:“你怎么不说话了?你不是很大度的吗?”
他声音沙哑,问我:“我有说不的权利吗?”
说完抬手要碰我的脸,我偏了偏头,躲了过去。
“碰你你也不喜欢,是吗?”他声音有点苦涩,却没把手放下,最后指尖依旧碰上了我的脸颊。
“心心,是不是你其实特别恨我,特别讨厌我?你那个时候那么小,我却不肯和你在一起,丢下你就走了。”
我眼眶酸涩,却强忍着不让眼泪涌出来,许砚说话让我觉得密密麻麻的痛意,他问我:“是不是真的来不及了?你真的不愿意喜欢我了吗?心心,你已经喜欢上别人了,是吗?”
我咬着唇不说话。
他想到什么,从口袋里拿出钱包来,从里边拿出一张东西,问我:“这个还有用吗?”
那是一张“有求必应卡”,上面还签着我的名字。
是十多年前,我随手送他的生日礼物之一。
他又继续从钱包拿出别的卡片,是“马上不生气卡”。
卡面字迹依旧清晰,被保存得很好,只是边角氧化泛黄。
自己年少时的签名青涩而简单,成为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许砚大概预想到了我说“没用”的答案,把我揽入怀中死死困住,他用的力气很大,仿佛这样就能让我们骨血相融,不再分离。
很久,我听到自己说:“许砚,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啊。”
“这种破东西干嘛还要留着。”
以及:“我好想你。”
“你能不能不要再走了。”
我眼泪终于在此刻落下来,起先只是很小声地啜泣,到后来却完全忍不住,趴在许砚胸口嚎啕大哭,如同无助幼儿一般,将他毛衣浸湿一片。
他的手臂如钢筋牢笼般把我困住,困在窄窄一处,把我的人,我的心,我的灵魂,悉数困住。
但有湿润的液体落在我耳侧,真怪,怎么我自己哭,会把眼泪流到这个位置。
哭到呼吸不畅的时候,许砚俯首和我接吻,泪水朦胧的余光中,我看到他的眼眶和我一样红。
我与许砚在多年前的雪灯祭前夕分开,兜兜转转,不曾想多年后的某个冬天,我们又在雪地冰天里重新牵手。
进那家omakase店面的之前,我问许砚:“这个店不是很难预约吗?”
他笑笑,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却是看到他进了店面,还算熟络地和主厨打了个招呼,我愣了一下,问:“你之前来过这儿?”
他承认了。
离店时,我不经意看到店门口有个小小的公用电话亭,这种街边便民设施如今在国内很难看到,我询问店家:“那个电话是可以拨通的,还是只是装饰品?”
众人随着我眼光望去,小馆店主还没答话,许砚却突然开口了:“可以拨通。”
“你怎么知道?”
他仿似在讲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嗯,因为有一年用它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我怔了一下:“什么时候?”
许砚帮我将围巾围好,我们没撑伞,札幌的雪势变大,有些积雪落在许砚宽阔的肩膀上。
“记不清了,大概是前几年吧。”
他语气轻松:“那段时间公司上市前夕,舆论缠身,负面报道很多。有天晚上出差,和合伙人在这儿吃了个饭。
“我大概是喝多了,当时特别想听听你的声音,就和餐厅老板借了两枚硬币,打了个电话给你。”
我摇摇头,在记忆里搜寻,却完全没有这段记录。
许砚笑笑,说:“你当然不会记得。你当时接起电话来,说‘您好,哪位’,我不敢说话,你在电话那头和别人说‘可能是诈骗电话吧’,然后就挂了。”
我心底钝痛,没忍住质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回来找我?”
“一开始是公司没做起来,后来呢?后来上市了,为什么也没见你出现?”
许砚平静阐述:“那时候你已经和余北在一起了,我不想打扰你好不容易回归平静的生活。”
“如果我没有和余北分手,你不会回来找我是吗?”
许砚不答,我知道他默认了答案。
“你没后悔过吗?”我换了个问题。
他摇头,很认真和我说:“心心,就算让我回到过去,给我一次再做选择的机会,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他说他没有办法保证自己能成功,不想让我冒这种风险,说应该用玻璃罩子罩住我,放在温室里精心细养。
我狠狠推了他一把,问他:“那你有想过我吗许砚?你有问过我的想法吗?我愿意陪着你的。”
他目光铮铮,强硬把我重新揽住,一字一顿说:“但我不愿意。”
“所以你把我抛下了,许砚,你能用我年少懵懂,分不清喜欢和陪伴的理由来糊弄我,你有没有想过我不是傻子,我十八岁想不明白的问题,难道我二十岁,二十五岁还会想不懂吗?”
怎么可能想不懂?怎么可能会判断不出什么是亲情什么是爱情?
对许砚的喜欢如同一场高烧,烧退了,夜以继日的想念和心痛却如后遗症一样难以消散。
我只知道不可能再有人对我百般纵容,不可能再有人圣诞夜为我赠上一个雪人,不可能有人在我漫长的青葱时光陪伴我走过所有道路。
我无需问,无需考证,也能在凌晨时分的不断反刍记忆中,明白许砚的占有欲,明白他的言不由衷,明白他曾那样喜欢我。
像我喜欢他那样。
是朋友之情,亲人之亲,更是爱人之间的喜欢。
许砚任由我推搡,却不放开我,我终于推累了,哑着声音问他:“我送的东西都留着,为什么我说过的话你却没放在心上?”
他问“什么”,我说:“我从前就一直说余北gay里gay气的,你难道一点都没印象吗?”
这下大概是轮到许砚大脑宕机。
“你……”
我仰头看他:“所以许砚,我也没有如你所愿地往前走往前看,我被困在原地,一直等你。”
许砚……许砚……我曾在旁人不知的无数深夜,在舌尖呢喃过这个名字数百次,每次想起,整颗心都要在油锅里滚过一次。
他紧紧抱住我,我问他:“你不觉得你还欠我道歉吗?”
他马上说“对不起”,声音也很苦涩,又很快说:“心心,我再也不走了。”
“以后我去哪儿都带着你,好不好。”
札幌雪灯明明灭灭,所有留存在岁月里的吉光片羽在此刻汇集,曾藏匿在圣诞漫天大雪中的小心翼翼的情愫,终于在多年后的冬季再次会面。
我终于拥有许砚。
正如许砚拥有我。
(《第八年冬》言言才不是傲娇受/著完)
主播:三七/搏君
编辑:阿菁

我爱了一整个青春的男孩,比旷野寂静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每天读点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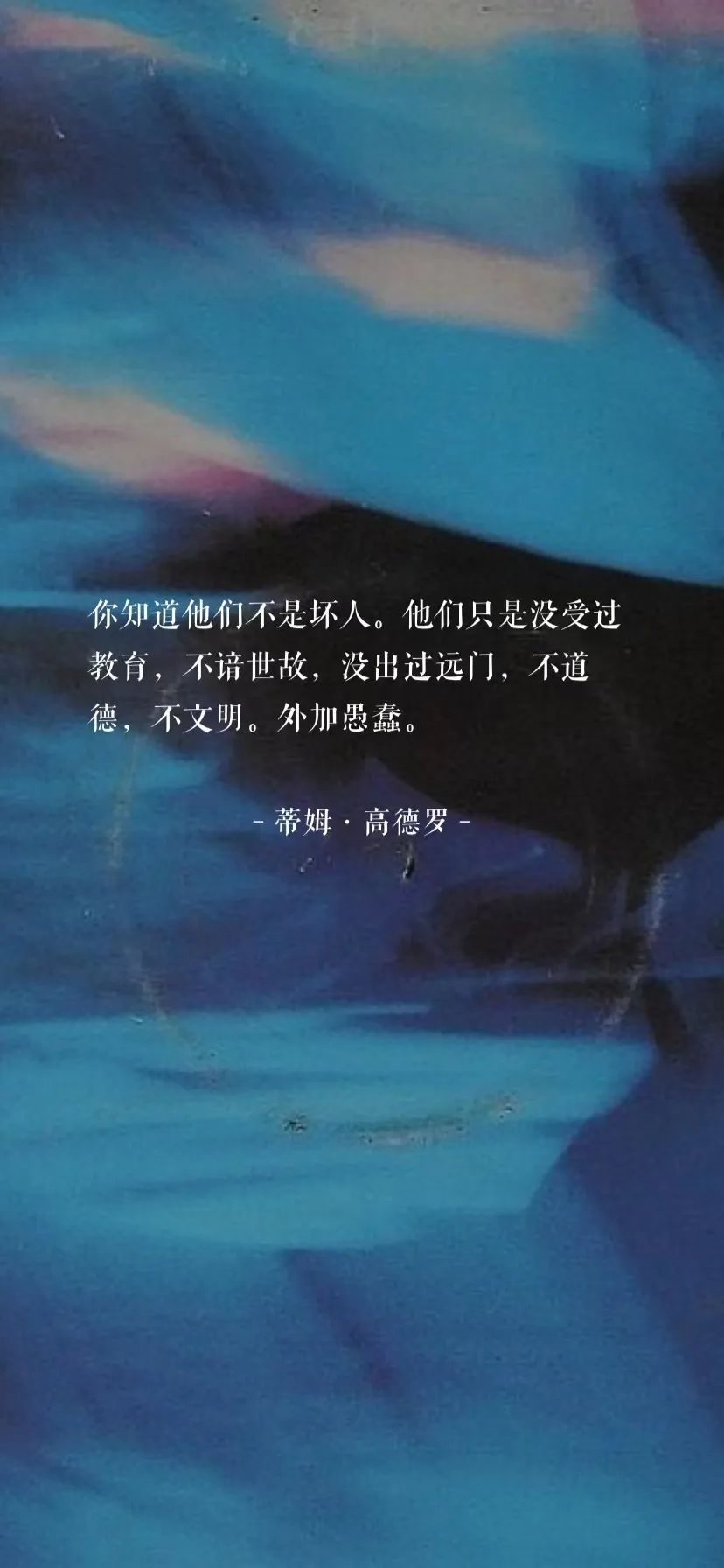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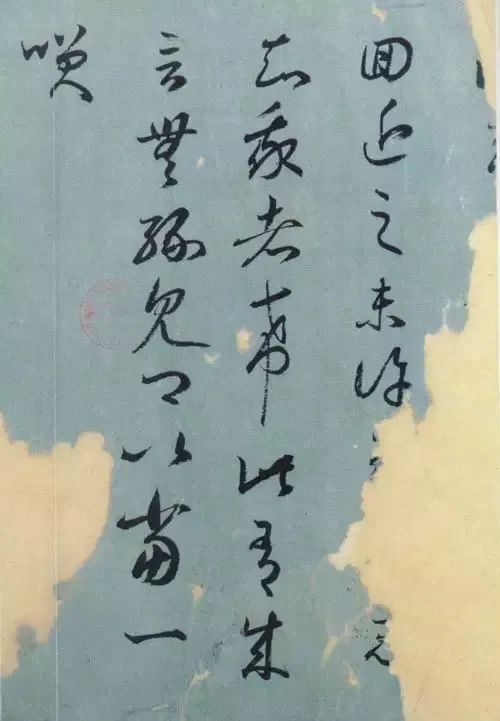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