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歌三人行
史上最纠结的音乐家,大概非柴科夫斯基莫属了。他经常要下很大的决心,去做微不足道的事情,而结果又总是懊悔不已。
他爱哭,动不动就在人群中啜泣乃至恸哭;他怕生人,随时想着要逃离学生,逃离学校,逃离城市;他好不容易结了一次婚,两个月之后就脚底抹油,不告而别。
音乐上也是,明明他是爱荣誉和名声的,可是荣誉和名声终于来了,他又希望世界把他忘记;明明他是自信和执拗的,可是评论一来——欧洲乐评家说他的音乐发臭——他立刻就满腹牢骚,天地失色。
一部作品明明很喜欢的,可他转身就讨厌起来;他信誓旦旦地说从此不写歌剧了,可是几个月后,一部伟大的歌剧就诞生了。
在我听来,他最纠结的作品,是一首 a 小调钢琴三重奏,名字叫《纪念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这个伟大的艺术家便是俄罗斯钢琴家、指挥家尼古拉·鲁宾斯坦。在他去世之后,老柴写了这首三重奏来纪念。
可是在这之前,老柴明明是很讨厌钢琴三重奏的。在给赞助人梅克夫人写信时,他说,他无法带着真正的感情来写一首三重奏,“小提琴和大提琴温暖的声音和乐器之王较量一下,就全失去了好处,而钢琴又一点没办法像它的对手似的高歌!”
老柴写信的时候,纠结得很。因为他知道,梅克夫人特别喜欢三重奏,而他也又特别希望自己能取悦于她,让她感到愉快。
老柴的另一个巨大的纠结在于与尼古拉·鲁宾斯坦的关系。事实上,他对谁都纠结,包括他的老师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也包括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李斯特和勃拉姆斯。尼古拉·鲁宾斯坦与老柴的关系,颇似舒曼一家与勃拉姆斯,不过没有那么复杂。
鲁宾斯坦是老柴的伯乐和恩人,是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校长,也是他的哥们——他最穷困潦倒时,尼古拉·鲁宾斯坦收留了他,把他聘为莫斯科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让他搬进自己的家,同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了六年。
老柴的作品,首演经常是鲁宾斯坦来完成,无论是生活上、精神上与音乐上,鲁宾斯坦都是老柴的知音,也是他最好的阐释者与传播者。他无条件信赖他,服从他,跟着他的牵引,他开始走向乐坛,走向大众,走向整个欧洲。
对于这一点,柴科夫斯基非常清楚,“谁也不会比他更清楚我的音乐人格,谁也不及他更能帮助我在西欧成名”。而同时,“这个特别的巨人,总是用一种不可接近的蛮横来对待我,谁也不比他更知道怎样伤害我的自尊心。”
鲁宾斯坦时不时地把老柴挑剔得体无完肤,甚至老柴要把那首最著名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献给他,他也大加贬斥。他们之间的差异无处不在,无论在生活习惯上、感情上还是对音乐的理解上。
鲁宾斯坦生性浪漫,喜欢热闹,爱出风头,钟情于华服和酒会,生活混乱。而老柴呢,他热爱孤独,喜欢离群索居,又多疑,敏感,固执,笨拙,神经质,虽然他在形式上依赖鲁宾斯坦,却时时想从他的保护下逃离出来。
梅克夫人对柴科夫斯基的赞助,其实是鲁宾斯坦出面去要到的。而最终也是她帮忙,让老柴搬出了鲁宾斯坦的家,最后连莫斯科音乐学院的老师也不干了。为此鲁宾斯坦大光其火,甚至要求梅克夫人取消对老柴的赞助,两人差点反目,二十年的友谊岌岌可危。
鲁宾斯坦在巴黎生病期间,老柴还写信给梅克夫人,对他颇有微词:“没有刺激和风头,他就简直不能生活,这是他的生命。他不喜欢念书,散步也使他苦恼,甚至他自己给自己弹奏音乐,也觉得毫无乐趣——必须有人在听他。”
可是不久,噩耗就传来了,鲁宾斯坦生病去世了,老柴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最重量级的知音。就像梅克夫人说的:“谁能够弹您的曲子像他弹得那样好呢?”
悲伤之下,纠结变成了动力。一首举世无双的悲歌由此诞生,老柴既取悦了梅克夫人,又向老友表达了最诚挚的怀念,同时也破除了自己心头的千千结——他说,我真佩服贝多芬、舒曼、门德尔松能写出注定难听、结果却并不难听的钢琴三重奏。
其实老柴怎么可能会失手呢,他正当盛年,技术纯熟得让大提琴、小提琴与钢琴的平衡和谐几至完美。事实上,人们把它看作是史上最优美、最伤感的钢琴三重奏之一,将它与贝多芬的大公三重奏、德沃夏克的杜姆卡三重奏相提并论。
老柴的神来之笔在第二乐章的变奏曲,主题用的是在 1873 年他与鲁宾斯坦、拉什金在莫斯科郊外郊游时,路遇的农民唱的民歌。那个时候,正是他与鲁宾斯坦相知甚笃的阶段。
十多次变奏,钢琴的悲怆,大提琴的忧郁,小提琴的心酸在其中发挥得得淋漓尽致,听起来就像三个性格不同的老朋友,执手相看泪眼,千言万语,切切嘈嘈,从此依依惜别,天各一方。
老柴的的一生,都在解决各种大纠结和小纠结——所谓的纠结,其实是他的内心自我和现实的紧张。通常的情况是,他越是牢骚满腹,越是彷徨犹豫,越是自我否定,他的作品就越是优美(比如那首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愈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冲突,表现在旋律上就愈是动人。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在俄罗斯的古典音乐中,他的作品流传最广,也最杰出和经典。因为只有纠结的音乐家,才是为内心而创作,最忠实于内心情感的——音乐史上没有哪一个音乐家,像柴科夫斯基那样做到只为内心而创作,连贝多芬也不能。
老柴一辈子只写过这唯一的一首三重奏。在其中,他似乎解开了自己的心结,却耗尽了一生的悲伤。与他众多宏大的悲怆的交响乐和协奏曲相比,这首 a 小调钢琴三重奏是一种低调的悲伤,一种挥之不去的伤感。有人说它的旋律优美,美得就像日落前的最后一抹余辉。
许多时候,我却听出来一种和解——一个音乐家在用他感伤的怀旧,纤弱的自怜,病态的内心分裂,向现实求和,求得宽容、原谅和理解。
事实上,在鲁宾斯坦去世以后,柴科夫斯基在人际关系上确实放松了许多。他的名字已经传遍了欧洲和北美,开始频频出访,参加各种形式的聚会。他不仅克服与生俱来的羞怯,亲自上台指挥自己的歌剧,还频频提携年轻的音乐家。他虽然还纠结,不时抑郁和伤感,但他的生活,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安详和快活。
在他写给梅克夫人的信里,不时出现高兴、愉快等字眼。可是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几年,梅克夫人的突然绝交又将他打回了原状——虽然他们未曾谋过面,可她几乎就是他的定海神针,是他物质和情感上双重引路人,他视她如神如仙如上帝”。
这场绝交在老柴心中掀起的无疑是一场毁灭性的情感风暴——纠结这个词用在这里已经太过轻渺——两年后,他完成了第六交响乐,给它命名为“悲怆”。紧接着,他死于霍乱。柴科夫斯基终于得到了解脱。其实,任何形式的爱都不能平息艺术家内心的强烈冲突,惟有死亡。
柴科夫斯基的死,让一个年轻的音乐家备受打击。他就是年仅 20 岁的拉赫玛尼诺夫。就像当年鲁宾斯坦兄弟提携自己一样,老柴对拉赫玛尼诺夫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和希望。
拉赫玛尼诺夫作为作曲家甫出江湖,老柴总是对他的作品褒奖有加,不仅帮他出版作品,让他和自己出现在同一张海报上。他的歌剧作品首演,老柴还特地坐到最显眼的包厢,让所有观众看到他在为新人喝采。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还说,为了让有天分的年轻人有出路,他甚至可以放弃作曲。
大师的提携与知遇之恩,为拉赫玛尼诺夫谱铺平了成功的道路。可惜好景不长。老柴的死,无异于泰山崩于眼前。在闻知噩耗的当晚,拉氏便仿照当年老柴悼念鲁宾斯坦的方式,谱下题名同为“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 d 小调钢琴三重奏。
拉赫玛尼诺夫与柴科夫斯基的的师生之情单纯,深厚,专注,他写给他的悲歌亦没有丝毫杂念。他在给友人写信时描述自己的作曲状态:“我以至诚、沉痛的心境来创作此曲,奉献上我所有的情感与力量……我为每个音符感到颤栗,有时甚至删掉所有的创作,构思又构思,乃又重新谱曲……”
身为老柴的嫡传弟子,拉赫玛尼诺夫性格上虽然不像老师那样纠结,但是他的忧郁、深情和丰盈,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音乐上,他与老柴的风格亦如出一辙,那就是——毫不羞于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情感,从来不曾为内心的情感遮遮掩掩。
他在老柴如歌般宛转悠扬的旋律之上,扩张音乐的力度和宽度,将情感体验进一步加深、拓展。“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老柴的 a 小调钢琴三重奏,死是一场告别,一种离殇;“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在拉氏的 d 小调钢琴三重奏中,死是一种永恒的打击和苦难,年年月月悲伤。
听拉氏悲歌的人都会有种被淹没和击中的感觉,像是一个极度悲伤的人,至始至终都把自己浸泡在眼泪里。从第一击钢琴敲出的泫然欲泣,到中间的潸然泪下,再到最后的一句乐音变成啜泣和呜咽。
拉赫玛尼诺夫巧妙地把老柴悲歌中的片段,融进了自己的音乐:老柴音犹在耳,让人想到岁月无情,当年为他人作送葬曲的人,今日却由他人为自己作挽歌。毕竟是年方二十的音乐家,情感如排山倒海般强烈。第二乐章的变奏,忧伤忽绵长忽简练,激烈和静谧互相缠绕,相互追逐。
变奏曲的主题旋律来自老柴特别欣赏的一部管弦乐幻想曲《岩石》——这是拉赫曼尼诺夫阅读契诃夫的小说《在路上》后,得到灵感而谱写的。在老柴去世前的那年夏天,他把它和《图画交响曲》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老柴当时还开玩笑说:真是后生可畏啊,自己在夏天才只写了一部小型的交响乐(即著名的第六交响乐《悲怆》)。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两首悲歌,前后相接,像是开拓出的一条时间的长河,将音乐史上的三个巨匠——鲁宾斯坦、柴科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他们的爱恨悲欢,以一种悲情的方式凝固成了永恒。
中国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我在想,三人行亦终有一别——我指的是鲁宾斯坦,柴科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也指那个一去永不返的浪漫主义时代。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美在高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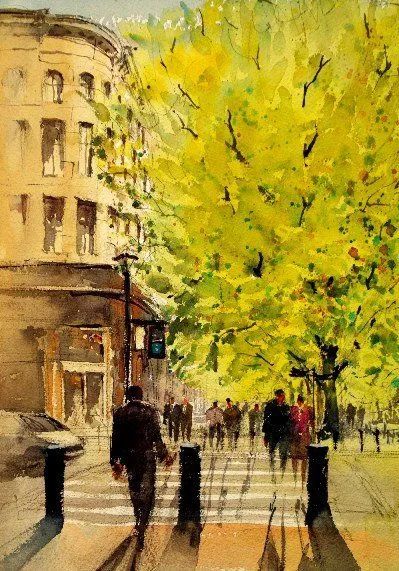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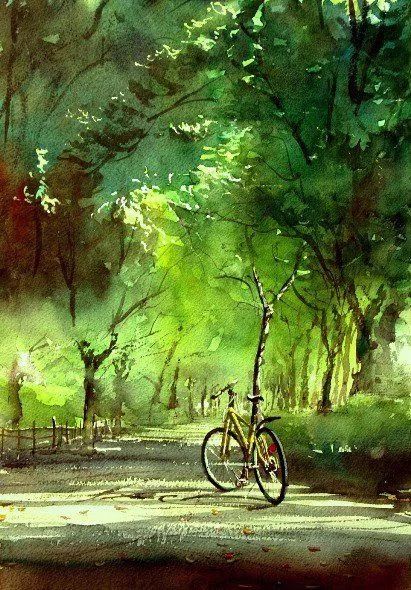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