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有什么用?

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的片刻。

身处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失声痛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此时,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 16 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他就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
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70 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纸巾。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止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四周多的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各奔东西,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四郎探母》,每一次都会遇见父老们和他们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懂了为什么《俄底浦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
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蘸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
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种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

于是,孤立的个人产生了归属感。那些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
“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

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或者对这段历史原本漠然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文化便成为它最重要的黏合剂。
本文选自龙应台《天长地久》,插图为北周莫高窟 428 窟人字披西披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美在高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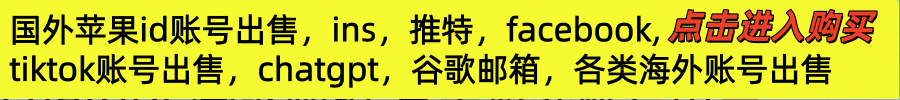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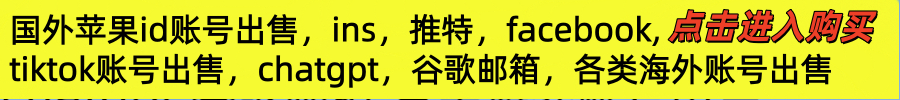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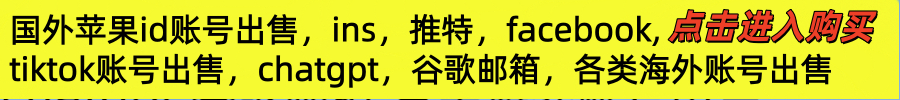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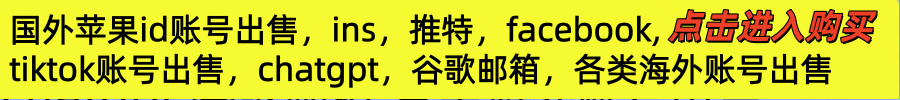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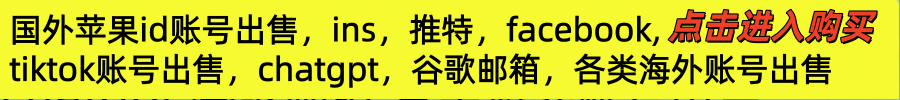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