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杀了,在考研成绩发布那晚
我自杀在考研成绩发布那一夜。
因为妈妈说,考不上研究生的小孩都该死。
跌下来了。
腿猛一蹬,我从瞌睡中惊醒,母亲正在外头用力敲门,我赶紧站起来,开门,她径直走进来,到镜子前头梳头。
她说:“上个厕所怎么这么费劲?”
我赔笑道:
“我睡着了。”
她从镜子里斜睨着我:
“这一会功夫还睡什么?不是血糖有问题了吧?哪天带你去查一下,真不让人省心,说了说了少玩手机少熬夜……”
我无言。
母亲并不需要看着我啰嗦,话语自有它的重量,于是有惯性,一句拖着一句掉出来,随便掉到什么地方,我只需要沉默。
她用力梳头。
她的头发掉的很多,梳子上摘下一卷发团来,丢进马桶里,枝枝蔓蔓,拉扯着不肯就被冲下去。
我放空发呆,直到母亲梳好头要出去,嫌我碍事,不耐烦地啧一声。
我惊醒,一步一步跟着她,闻到她身上温热的香,像母鸡翅膀下一只小鸡,忽然有种温柔错觉。
于是问她:
“妈,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
母亲说:“威胁谁呢?还要死,要死就去死,谁管你。”
我鼻子一酸,但是说:
“那我就放心了。”
她要做饭了。
我躲回房间,落锁。
吃饭如今是我最大的难题,我不知道怎么伪装进食,同样我也不需要如厕,饮水,更不存在血糖的问题。
只不知为什么,睡眠仍缠着我。
又或许,死亡本身就是长久的睡眠,生人的睡眠不过是死亡的潮汐侵蚀,涌上来,褪下去。
我已死。
慢慢地,我对镜解开衣扣端详。
我的皮肤是喜庆的嫣红色,一氧化碳中毒的显著特征。
我是烧炭死的。
特别温暖,特别困顿,一氧化碳渐渐替代氧气,占据我的肺部。
溺水样的痛苦袭来,我大张着嘴,在精神中挣扎,身体却一动不动。
痛。
没有任何一种死亡是不痛的,每一处正常运转的器官忽然遭受灭顶之灾,由健康骤然衰竭,企图以剧烈的痛楚提醒宿主,悬崖勒马。
炭火渐渐冷却。
我的身体渐渐冷却。
一生中所幻想过的,最坏的事情,我的肉体死亡,但精神犹存。
我清楚感知到尸僵的发展,从下颌,到两腮,脖子,肩膀,手臂,脚尖,双眼无法合拢。
呆呆的,我望着自己的枕套,那里有一朵绣花。
一百三十五针。
口不能言,身不能动。
无上的恐惧笼罩我,此刻如果有人发现我,我将在感官完整,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被送去火化。
第二次死亡。
又或许依旧不会死,要亲人用那把锤子将我浑身骨骼敲得粉碎,装进狭小木盒中。
不见天日,以水泥浇灌永世的牢房。
我的牙齿咬得死紧。
我咬牙得发出吱吱声响,泪腺停摆,我已不能流泪,恐惧和痛苦下,只能在心里一遍一遍叫。
妈妈。
一个人最初也是最后的声音。
妈妈。
我后悔了。
我和母亲的关系并不怎么好。
这是在尸僵缓解后,我能坐在床头的时候,精疲力尽想的。
大学毕业之后,我一直漂在这座城市,住在一间阁楼,三角形的房间。
天花板与地面从没想过有交汇的一天,正如我没想过,与这样的生活会纠缠不休。
我做一份价值三千三百五十八元的工作。
城市里的人是没有价值的。
工作的价码,是购买TA肉体与精神的打包价,于是我理所应当的,变成一件廉价商品。
母亲并不满意。
没有什么投资者能接受自己二十二年的长线投资以亏本告终,但幸而这份投资是活物,仍可追加鞭策。
第一次考研失败。
那年春节,母亲破天荒的没有催促我出门拜年。
我乐得自在,下楼买饮料时遇见邻居,寒暄到学业工作,我瞥见她忽然色变。
一种压抑的,耻辱的表情。
我忽然噤声。
她以我为耻。
家里的条件一般,我曾是她光鲜的衣,是她指头颈项缺乏的金,一朝褪色,比穷困更潦倒。
她以我为耻。
盆里的炭早已成灰,却有半张纸始终没被烧到。
我僵硬挪过去,看见我的名字,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全都逃过一劫。
连分数都没被烧掉。
像命运特别怀有恶意,一夜的炭火,偏偏叫它幸存,我看见二百九十八的分数,已死的身体忽然也寒冷彻骨。
那是比第一次还要低三十分的成绩。
又到年关,欠债的人难过年。
我欠母亲一份成绩。
但,人死账消……
我用湿毛巾封死了阁楼的窗与门,在不锈钢盆里倒满炭,想一想,把成绩单丢进去,躺到床上,又负气地,转过身,把脸埋进枕头。
有许多理由和借口。
上考场的时候,我正发烧三十九度二,咽如刀割,某种病毒正肆意折辱我肉体,每一节骨骼,每一寸皮肤,我在考场的卫生间里呕吐。
但,自怜的话,没有人想听。
再过十年。
他人只会记住你两次考研的失败,没人会特意提起,有多少努力,有多少困难。
可我已经死了。
我呆呆坐在床头,两天一夜,手机上并没有任何骚动,只有母亲发消息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我忽然极软弱,极眷恋,浑忘全部旧恨,拨打母亲电话号码,几乎迫不及待问她:
“妈妈,我现在就回家好吗?”
饭做好了。
母亲叫我吃饭,自己却回了房间,说没有胃口,我夹起饭菜,咀嚼,然后偷偷吐在垃圾袋里。
不能被母亲发现我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这样。
在传统故事中,有些鬼魅不知死而活,不然心愿未了,也可滞留人间,偏偏我不属于任何一类。
母亲在房间里问我:“吃完了吗?”
我说:“嗯。”
我不是个擅长撒谎的人。
她说:“对了,你分数出来了吗?”
我停跳的心脏忽然一跌,颤栗道:“没有。”
她没怀疑,说:“那下午陪我去庙里吧,拜拜文曲星,保佑你这次能考上。”
我说:“人那么多,现在疫情还很严重,别去了。”
她忽然顽固道:“去。”
我无言垂首,沉默望着地砖,白色的,上面一曲一曲的,全是她的头发。
我蹲下去,把它们抿到手里,居然能搓成一球,像猫毛一样,一大团。
我说:“妈你怎么掉这么多头发?”
她说:“天天跟你操心,还有不掉头发的?看见了就捡起来,眼睛里有点活,一天天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她又说:
“你自己觉得这次考的怎么样?”
我的喉咙像被毛球堵着,扎扎的,说不出来话。
谎言最后都将被拆穿。
知道我自杀身亡,妈妈又会怎么说?
她素来看不起自杀者,笃定他们是无能弱者,其中,最瞧不起自杀的青少年。
她会说:“这点压力都受不了还能干什么?太自私了,死的时候考虑过父母吗?”
我偏偏无法反驳她。
盖因她是十二分苦楚中闯出来的女人。
她很早就失去自己父母,我出生后,我父亲即患急性胰腺癌过世。
这是一种良善的恶病。
快。
极快。
不会细水长流消磨你的金钱,也不会用虚假的好转哄骗你的精神,它来,只告知你一个字。
死。
母亲忽然又落得孑然一身,更可怕的是,拖带一个无知婴儿,每日哭泣数十遍,为吃,为穿,为爱。
她一样都给不了。
我无法想象她如何将我养大,靠一台缝纫机。
暴躁与深爱。
我臣服于命运,不得苛求她在极度困苦下,超越那一代父母。
但我仍会受伤。
理解不能消解痛苦,正如在医生面前说你爱Ta无用,不能抵扣治疗费用。
她千辛万苦。
我千疮百孔。
我忽然笑道:“妈妈,我也大了,你有合适的,再找一个吧。”
我到底要走的。
不管好,还是坏,在我走后,希望妈妈能与人间还有些联系。
孑然一身,对中年人来说,究竟不祥。
母亲已经穿好衣服出来,有点诧异,啐了我一口,又作势要拍我:
“换衣服去,我疯了是不是,好大年纪给自己找个人,图什么?为了伺候他?”
我嬉皮笑脸躲了,笑道:“是啊。”
爱与恨都能让人活下去。
被照顾与照顾都是活着的理由。
我蹲下来替她提鞋子。
妈妈,死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女儿已经替你淌过这趟河了。
我只希望你离这条河远一点。
再远一点。
母亲一直拉我的手。
她走在外侧。
老家的冬天滴水成冰,路上的雪被车碾成一路冰壳,交通事故频发,她从来没走过里侧,她的手汗津津的。
我说:“妈,你怎么这么能出汗?”
她不动声色道:“穿多了吧。”
我说:“手冰凉,穿什么多?”
她的汗也奇怪,冰凉滑腻,她发觉我在摸她的手,甩脱我,不耐烦地拍了我一下:“手套带上,凉。”
庙里香火很旺。
我向来不相信这些东西,但今日着实心虚,不敢进门,只摆臭脸。
母亲居然破天荒的没指责我,只叫我在外面等着。
山上一直有车子开上来。
奔驰宝马是司空见惯,我看见玛莎拉蒂的车标还是吃惊。
车子一停,立刻有小沙弥奔上来开门,恭恭敬敬用手抵着门框,我不屑,冷哼一声。
谁说佛门清净?
到头来,依旧是尘世俘虏。
车上下来一个褐衣和尚,眉毛雪白,老态龙钟。
我愕然,心想如今的和尚未免太过猖狂,偷眼瞄着他,不料他居然也看中我,慢慢踱过来。
后面跟着一串大小僧众。
我紧张得皮肤都绷紧,直愣愣看着他,他走到我面前,端详我:
“小施主,又见面了。”
我反问:
“我见过您?”
他凝视我面孔:
“我见过你的照片,你母亲在庙里为你点了一盏二十年的长明灯。”
我的脸一瞬间垮下去。
这种地方做事,要多少钱可想而知,母亲那点血汗钱,最终也不过是成了玛莎拉蒂的一滴汽油。
我当真要发火,又不能对外人,在庙外咬牙切齿一个多小时,母亲才出来。
一出来我就质问她:
“你在庙里给我点什么长明灯?”
母亲两膝全是灰尘,一边用手套拍,一边没好气答对我:
“祈求你能考上研究生。”
我忽的气不打一处来:
“花了多少钱?”
母亲说:“我自己的钱,爱怎么花你别管。”
我指着她,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感激死亡让我不能流泪。
我说:
“妈妈,钱很要紧,以后我在外面照顾不到你的时候,你老了,你怎么办呢?”
母亲皱眉:“我去死。”
“不要说这种话!”
我几乎在吼。
但她不会懂。
忽的一阵委屈袭上心头,我问她:
“考不上研的生活会毁灭吗?考不上研究生的人都该死吗?有那么多人连大学都没有读,不也能好好的过一辈子吗?为什么——”
“该死。”
她斩钉截铁打断我。
“现在的学历都在贬值了,你想找一份好的工作,本科学历根本就不够,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呢?你想怎么过呢?”
我一步一步往后退。
母亲说考不上研的人都该死。
一种自毁的快感涌上来,我想吐,但五脏已经僵化,我看着她笑,残忍的冲动反刍上来。
我应该剥落自己的衣服,让她观赏我的尸斑。
我将绘声绘色地告诉她,死亡那一刻我承受了什么样的痛苦,看她痛哭流涕,追悔莫及。
但我什么都没说。
我转身走了。
我没有资格恨任何人。
要恨的话,只能恨自己死而不僵。
我无处可去。
落魄时候,特别难见人,要人家高兴见你,还要你抹得开面子见人家。
往往不能两全。
我最终给高中同学打电话。
他是个矮胖男生,姓于,于帆,形容平庸,资材低下,只有一把好脾气。
因为不可能得到异性的爱,所以反而人缘奇佳。
我说:“出来聚聚?”
他电话里很嘈杂,大概是跟家人在一起,我听见他说:“好。”
他是开车来的。
我说:“走走?”
他说:“带你去散散心。”
我说:“我看起来就那么不开心?”
他笑而不语,良久,冲我伸出手,说:
“你很坚强了。”
我浑身忽然一软。
一个人往往不怕死,不怕牺牲,但怕死无人知,白白吃苦。
我的鼻子酸得要死,一滴泪都流不出来,颤抖着说:
“谢谢你。”
却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知己。
他说:
“我们是朋友。”
我惭愧低头。
他开车带我去桥上。
天空地阔,水面清气吹来,有点腥凉,但清爽,我絮絮叨叨,他无言听我讲。
我说:
“我去年十一月的时候,为了学习通了个宵,早晨实在撑不住了,趴着睡了二十分钟,左手瘫痪了,是神经性损伤。”
茫茫然的我说:
“真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
他说:“你得撑住,阿姨只有你了。”
我的胸口被巨大的悲伤摄住,我低头:
“没关系,她不需要我这样的废物女儿。”
他轻轻说:“怎么会呢?你在我心里一直都很优秀,很独立,这一点点失败,在你的人生中能占多少分量呢?一个人现在至少能活到七十岁呢。”
老套的安慰,但我特别受用。
许久没人说过我能行。
母亲最爱说的是完了,毁了,一辈子都没用了,没人告诉我,你能活七十年,一两年的失败不算什么。
我忽然神经质道:
“假如我死了,你会想我么?”
他轻轻说:
“我会痛不欲生。”
我心一热:
“多谢你。”
他看我的眼神极温柔,又忽然叹气。
他说:
“在我的角度,要感谢命运如此薄待你,否则一世无机会对你讲,我喜欢你很多年。”
我苦笑。
我的肉体已死。
他爱着衣冠楚楚的我,不过是我另一副面具。
我沉默不语。
他自觉过界,噤声,送我回家,又不甘心道:
“你讨厌我?”
我摇头。
他松了口气:
“以后阿姨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找我,着急去医院什么的。”
我说:
“好端端的,去什么医院?”
他面色古怪。
我察觉异样,追问他:
“我妈怎么了?”
他说:
“你……不知道?”
我盯着他眼睛。
他眼神闪躲一会儿,终于自暴自弃道:
“她在化疗,我妈他们都知道,才告诉我的,你不知道?”
我上楼的时候母亲已经在家了,她看我一眼,若无其事道:
“晚上想吃什么?”
我说:
“什么都不吃。”
她伸手探我额头:
“怎么不吃饭?难受?”
我猛往后躲。
不运动的部位,手感已经变得古怪,缓慢的腐败进程中,失去弹性,变得腻软。
我不敢叫她摸出端倪。
她讶异:
“躲什么?你从小就笨,自己发烧不发烧都搞不清楚,长这么大除了生病,什么时候说过不吃饭的话?”
我说:
“妈,把我养大很不容易吧。”
她说:
“没什么,妈也没把你养好,养得身体也不好,本来生下来好好的。”
我恍惚地笑。
但,依旧会说出让我去死的话。
世上的母亲大抵都是胃口愈来愈大的,刚出生的时候,得到幼儿一个笑,已经心满意足,到后来,指天要地。
有谁会对着学走路的孩子说,考不上研,就去死吧?
都是她。
爱我与恨我至深的人,一体双面。
我说:“你痛吗?”
母亲投来探询的目光,强笑道:
“说什么呢?”
我说:“掉了那么多头发,痛吗?”
她不讲话,手搭着椅背,居然有种犯了错被捉住的窘迫,眼睛惶恐抬起来:“你知道了?”
我说:“下次我陪你去。”
她说:“别来了,难看。”
她一辈子要强。
是痛也好,苦也好,眼泪,血汗,从不肯让我看见,在我面前,她永远是顶天立地的妈妈。
又怎么能责怪她觉得我是个脆弱的废物?
我没跟她顶,我说:
“好,我不去。”
我去了庙里。
大着胆子,我踏进门槛,买了一束香,这是工作日,人并不多,我敬上香,长跪不起。
我甚至不知道面前这一尊神姓甚名谁,我只祈求自己的身体,再晚一些腐烂,让我再照顾母亲一些日子。
面前忽然一暗。
老和尚慢慢走过来,正挡住长明灯的亮儿,他注视我,忽然伸手拔了我的香。
我瞪他。
他无声地笑了,白胡子一把,有点调皮的,挑眉看我,低声道:
“小施主,这是自投罗网。”
我瞪着他说不出来话,他笑嘻嘻灭了我的香,往后一指:
“外面坐坐?”
我乖乖跟他走了。
他连口水都没让我,自顾自喝了一大口热水,我反而敬畏,自觉已被看破,静静等他开口。
“小施主。”
他说:
“令堂给你点了一盏长明灯。”
我说:“我知道,祈祷我能考上研究生的。”
他笑道:“哎,母亲为女儿所求,怎么会是如此俗物?”
我说:“那是什么?”
他端详我,不讲话。
我愕然。
他看我的脸,又看我唯一露出来的手,道:“小施主着实遭了点罪。”
我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用手一抹,是红色。
是血。
我已经无泪可流,只剩流血。
他静静说:
“令堂求你长命百岁,健健康康。”
我就笑。
我说:“这样也能算长命百岁么?”
他说:“人怕心魔,小施主心中有魔,令堂心中有魔。”
我说:“那么,我还是人么?”
他笑而不语。
我悲哀地,笑着,流下两行血来。
我说:“她爱我。”
他说:“她爱你,她许愿让女儿受的磨难都转移到自己身上来,让你一辈子顺顺利利。”
我软弱道:
“我不知道。”
他说:“世人往往如此,人前逞强斗狠,人后吐露真情。”
我说:“你会把我的灯熄掉吗?”
老和尚站了起来,褐色僧袍被山风卷得飒飒作响,我第一次见他如此正经,他双手合十,念了句佛:
“阿弥陀佛。”
“事已至此,并不在于那盏灯是否亮着。”
他的脸上露出深远的悲悯,他的眼睛像辽远天空。
他说:
“去见见令堂吧。”
我发抖:
“现在?”
他颔首。
我几乎是跳起来,狂奔,左脚绊在门槛上,结结实实摔了一下子,不痛,更顾不得。
我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形容狼狈。
出山门的时候摔了一跤,额头上没了一块苟延残喘的皮,下车时候被车门夹了手指,两个指甲脱落,倘若不是冬季衣服厚重,早被人发现是一具行尸。
医院也有打电话过来。
但,无非是那些话。
任何一种病都有忽然恶化的风险,况且是癌症化疗。
我从没想过她步父亲后尘。
医院里特别拥挤,这段日子都是发热咳嗽的病人,我没带口罩,像个不怕死的异类,来来往往的人都要看我一眼,我顾不得,横冲直撞。
妈妈躺在某一间病房里。
我慌了神,一间一间探头找妈妈,护士看不下去,拦着我问了名姓,引我到里面。
我看见妈妈安静躺着。
她一直是个勇敢的女人。
面对死亡也一样,不像我,在犹豫恐惧中来回挣扎,我看见她安静的,几乎是闲适地躺着,我忽然停住脚,找到一个口罩,带好,又推到额头上。
我说:“妈,我来了。”
她说:“好。”
她的眼睛异常的亮,精神异常的亢奋。
我说:“妈。”
她说:“哎。”
我说:“妈妈。”
她说:“宝宝。”
忽然她眼泪涌出来。
我不敢哭。
我的眼泪是红色的血。
她抓住我的手摩挲:
“宝宝,妈真不放心你。”
我曾经拒绝她叫我宝宝,二十五岁的人,还是妈妈的宝宝,十分难堪。
但她摩挲着我的手臂,万分珍爱,我跪在床边,说:
“妈妈,宝宝在这呢。”
她说:“咱们家的存折……”
我说:“我都知道。”
她略松了松心,费力地喘了一会气,又道:
“今年考研落榜了吧。”
我无言。
她说:
“我知道你,打小儿考试不好了回家就是蔫的,不敢说话,你这次回家连说话都不敢大声,我就知道,又完了。”
我说:“妈,对不起。”
她说:
“你没有对不起妈的,都是妈对不起你。”
她的眼泪沿着脸往枕头里淌。
“小时候为了让你学习,那么打你,妈也不想,可是你一个人,在这世上……怎么办呢?”
我木木的,微笑。
死亡于我二人之间,应是重逢。
她说:
“考不上就考不上,别把自己逼出病了,妈妈不在了,对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活着。”
我的胃比大脑早一步反应,忽然剧烈翻腾起来,我呕吐。
干枯的胃囊翻不出任何东西,我只是吐。
一种极度的,生理性的痛楚席卷我的身体,我浑身痉挛着痛,为这突如其来的赦免,像一具电椅上的尸体等来了无罪的判决书,我蜷缩在地上,双眼圆睁。
我是无罪的。
可是,妈妈。
为什么,为什么不肯早一点,说出这句话呢?
为什么不肯早一点赦免我呢?
在。
在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
炭火渐渐冷却。
一具身体渐渐冷却。
床上的手机一直在响,响了又停,停了又响。
一天之后,偶尔响起。
两天之后,已认命般沉寂。
女警拿起死者的手机,发现这五十余个未接来电,用自己的电话打了回去。
“您好,珠江派出所。”
对面顿一顿:
“您好,仁爱医院。”
有两个女人在前夜死去了。
一个是母亲。
一个是女儿。
黄珍的身体被搬动,她是面朝下自杀的,遗书放在桌子上,等待鉴定。
很简短,她写:
屡战屡败,无颜见人,自行了断。
她的母亲黄爱华死于癌症并发症。
黄珍的死因较为明确,鲜红色皮肤,都是一氧化碳中毒的典型症状,她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房东恨得破口大骂。
但,他们看到这个女孩子脸上有笑容。
微笑的,与病理性肌肉拉扯不同的,她舒展的笑容,几乎有神性。
辽远的,空荡的,她笑。
房东打了个寒战,不情不愿地噤声。
在遥远的地方,一盏油灯打了个忽闪。
没有风。
金身慈眉善目地望下来,望着膝前一片又一片的油灯,大殿空寂,青砖冷沁,那盏灯虚弱的,又打起精神来,一星星火苗,直直举起。
一绺烟望上走。
似乎撩动了神像的白眉,他微笑着,宁静的,遥远的。
那盏灯下压着红纸。
上面写着:
“黄爱华为女黄珍恳求一生平安幸福快乐健康”
二十年的长明灯。
(《行尸走肉回乡记》碧仙/著完)
编辑:清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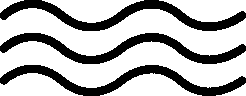
签完离婚协议,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每天读点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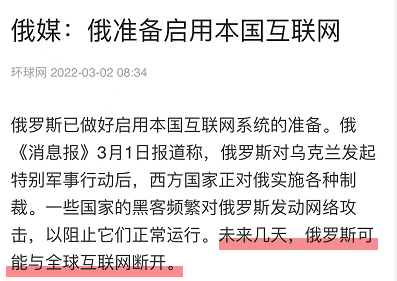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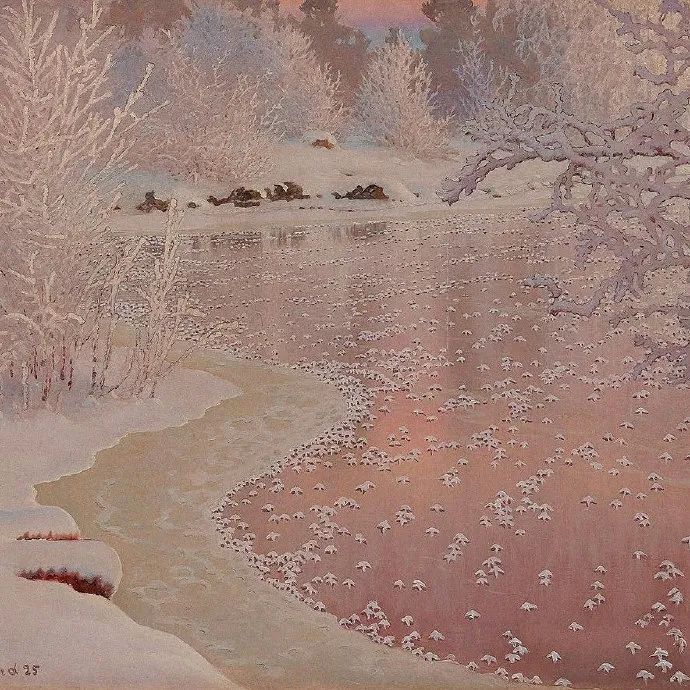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